前一章展示了我們常會忽略的一些影響到我們的判斷和行為的刺激,它們看似無關緊要、偶然發生,也很難被注意到。不幸的是,我們總會對這些偶發或轉瞬即逝的因素扮演的角色視而不見,而它們實際上是我們進行判斷和行動的重要推手。特別是,我們常會低估(或者根本就忽視了)一些最重要的情境性因素對我們的行為和信仰的巨大影響力。
這種「情境盲區」(context blindness)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我們會誇大個人因素的影響力,即「內在的」因素——偏好、個人性格特點、能力、計劃和動機——對特定情境中的行為的影響。
甚至在我們試圖分析自己做判斷的根據和產生某種行為的原因時,我們也會忽略情境因素並且誇大個人內在因素。在我們分析他人行為的原因時,問題會更嚴重。如果我們想形成某種判斷或者採取某種行動,我們就必須注意情境當中的各種因素。然而,對於他人面對的情境,我們觀察起來會頗為費力。因此,我們更有可能在分析他人行為時,低估情境的影響力,而高估他們的個人內在因素。
我相信,對於這種「低估情境、高估個人因素」的事實缺乏認識是人們會犯下的最普遍、最嚴重的思考推理上的錯誤。社會心理學家李·羅斯將這種現象定命為「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在實際生活中,犯下這種謬誤的人之間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性。這便解釋了對於更具質疑文化背景的人們而言,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避免這類錯誤。
基本歸因謬誤
比爾·蓋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19歲從哈佛大學退學,創辦了微軟公司。在很短的幾年時間內,他讓微軟公司成為世界上贏利能力最強的公司。人們可能由此判斷他一定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之一。
毋庸置疑,蓋茨當然極其優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進入大學以前就沉浸在計算機語言的汪洋大海中了。1968年,他是西雅圖一所公立學校八年級的學生,但對自己的功課已感到厭倦。因此,他的父母讓他轉入了另一所私立學校,而這所新學校恰好擁有一個連接到美國國家計算機系統主機的終端。蓋茨加入了一個小組,和他的朋友們花費了大量時間探索這台高性能的計算機。他的好運氣在接下來的6年中一直持續。他獲准幫助當地一家公司測試軟件,從而換取自由編程的時間。他常在凌晨3點從家裡溜出來,進入華盛頓大學的計算機中心,利用該中心那段對公眾開放的時間使用計算機。這個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少年會有像蓋茨這樣的條件接觸計算機。
在每一個成功者的身後都有一系列我們並不知道的幸運。如果經濟學家史密斯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篇數是經濟學家瓊斯的兩倍,那麼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史密斯比瓊斯更有天賦,並且更加勤奮。但實際上,如果經濟學家在「大年」取得博士學位,就意味著會有許多大學的教職虛位以待,他們會在學術市場上表現得更好,擁有更成功的學術生涯;相反,那些在「小年」取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的運氣就不會這麼好了。史密斯與瓊斯成功與否的差別可能更多會與純粹的運氣而不是自身的智力有關,但我們都沒有看清這一點。
許多在新世紀美國經濟大衰退時期獲得學位的大學畢業生可能終其一生都在苦苦掙扎,命運不濟。失業狀況十分殘酷,不只是因為這些人灰心喪氣找不到工作,而且因為經濟回暖似乎也遙遙無期。父母們會迷惑,他們那2009年從大學畢業的孩子簡為何如此命途多舛,而2004年大學畢業的瓊則在事業上做得風生水起。
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會隱藏起來,即使那些對我們的行為影響最大的情境性決定因素就在眼前,我們可能也會對其作用視而不見。
在20世紀60年代的一個經典實驗中,社會心理學家愛德華·瓊斯和維克多·哈里斯向實驗對像展示了兩篇論述古巴政治制度的論文中的一篇,這兩篇論文據說都是由一位大學生為完成一位教授的要求而寫就的。一篇論文支持古巴的政治制度,而另一篇論文持反對態度。研究者告訴讀過支持古巴那篇文章的實驗對象,這篇文章是一份作業:一位教授政治哲學的教師(在另一個實驗中,是一位辯論隊教練)要求學生寫一篇支持古巴的論文。研究者告訴另外的實驗對象,寫出了反對古巴政策的學生是被要求寫這樣一篇持反對立場的文章的。我想,我們應該會同意,實驗對象並沒有因此而瞭解這些學生對古巴的真實態度,儘管,這些實驗對像會評定寫第一篇文章的學生實際上更加支持古巴。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忽略同樣一些對人們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在斯坦福大學長期教授兩門本科課程。一門是統計學課程,另一門是社區服務課程。修讀他統計學課程的學生在學期末的課程測評中給他的評價是嚴苛、缺乏幽默感、異常冷漠。那些選修他社區服務課程的學生則評價他思維敏捷、有趣、十分溫暖。
無論你有英雄主義情結還是缺乏勇氣,這些都可能取決於具體的情境因素,它們的影響力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社會心理學家約翰·達利和比伯·拉塔奈做了一系列實驗研究後來廣為人知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intervention)。他們設計了一些看上去是緊急情況的場景——癲癇病患者突然發病,隔壁房間裡一個書架倒在了一個人的身上,一個人在地鐵裡暈倒了。人們會給這些「受害者」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極大地取決於其他人的存在情況。如果人們認為自己是唯一的目擊者,他們通常會施予援手。如果現場還有另外一個「目擊者」(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同謀),選擇上前幫忙的人會少一些。如果有許多「目擊者」的話,人們則幾乎不會提供幫助了。
在達利和拉塔奈的「突發情況」實驗中,參與者可以通過對講機和外部交流。當實驗對像以為事發現場只有他們自己時,有86%的人會急切地幫助「受害者」。如果他們認為現場共有兩個旁觀者,62%的人會提供幫助。當現場有四個人聽到了呼救聲時,則只有31%的實驗對像會去伸手幫忙。
為了更好地理解善意和對他人的關心這兩種內在因素可能不如情境性因素重要,達利和他的同事丹尼爾·巴特森以學習神學的學生為實驗對像進行了一項研究——人們一般會認為學神學的人更有可能對處於困境中的人施予援手。研究者讓一些普林斯頓大學神學系的學生到校園裡的一棟教學樓裡向好撒馬利亞人布道,告訴他們一些可行的途徑。其中一些學生被告知,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到教學樓那兒去;另一些學生則被告知,他們已經遲到了。在這些學生前去布道的途中,他們每個人都會經過一條走廊,走廊裡坐著一個人,他低著頭,不斷地呻吟和咳嗽,明顯需要救助。在那些不用趕時間的學生中,幾乎有2/3的人給那個人提供了幫助。而在知道自己已經遲到的學生中,只有10%的人上前幫忙。
當然,如果你只知道某一個神學系的學生幫助了他人,而另一個人沒有,你可能會對幫助他人的那個人有更好的印象。那種匆匆忙忙的情境不太可能發生在你身上,就像存在某種因素會讓一個神學系的學生無法成為一個好撒馬利亞人一樣。事實上,當你對人們描述這個實驗的情境設置時,他們並不認為這(遲到與否)會對一個神學系的學生是否會幫助一個在困境中的人有任何影響。鑒於此,這些人會把那些學生沒有助人歸因於他們糟糕的個人屬性——個人的內在性格之類。
隱藏的情境因素可能也會影響一個人能否發揮其聰明才智。社會心理學家李·羅斯和他的同事邀請一些學生參與一項研究,這個研究是以電視智力競猜節目的形式進行的。他們要求一個被隨機選出的學生提出問題,而其他學生回答他的問題。提問者要提出10個「有挑戰性但並非不可解的問題」,而「參賽者」需要大聲作答。提問者可以充分利用他們的特權在問題中涉及各種偏門冷知識。「從鯨魚身上提取的、聞上去甜甜的、呈蠟狀的,並且可用於製作香水的東西是什麼?」(是龍涎香——除非最近讀過《白鯨》的話)參賽者們最終只回答出了所有問題中的一小部分。
在這個實驗的最後階段,雙方參與者(提問者與回答者)和研究者都被要求分別對提問者和回答者大體的知識水平狀況進行評分。你可能會認為,結果很清楚,即因為提問者的角色在實驗中佔了很大便宜,所以實驗對象與研究者都會對他們評價較高。提問者的角色保證了他們不會暴露知識中的盲區,而答題者則沒有機會有選擇地展示自己。然而,所謂的提問者的優勢並沒有讓人們(無論是答題者還是研究者)明顯地給出「提問者有極其淵博的知識儲備」這樣的判斷。答題者和研究者只是認為,提問者的知識量比答題者多了一點兒,或者是比大學生們的「平均水平」高了一點兒。
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見到與這個答題研究(反映出的問題)相關性很強的事例。組織心理學家羅納德·漢弗萊在實驗室中設置了一個微型商業公司的辦公室環境。他告訴實驗對象,他很有興趣研究一下「人們在辦公室環境下如何共同工作」。他用了一個向所有人公開的隨機方法選取了一些實驗對像作為「經理」,並賦予他們監督的責任。另一些人則僅僅被設定為「職員」,聽從經理的命令。漢弗萊給經理們一些時間學習他們的任務手冊。在經理們閱讀期間,研究者給職員們展示了一些類似郵箱、文件存檔系統的東西。接下來,這個新組成的辦公室團隊要在一起辦公兩個小時。經理會給職員佈置各種各樣的不需要什麼技巧的、重複性的工作去做,而且職員的自主權很少。就像在真正的辦公室中一樣,經理會恰如其分地做一些高技術含量的工作,並指揮著職員的行動。
在工作的最後階段,經理和職員會為自己和對方在基於其角色的各種特點打分。這些特點包括領導力、智力、克服困難的能力、決策力、支持力。對所有這些特點,經理對自己的同伴(其他經理)的評分要高於他們對職員的評分。除了克服困難的能力這一項,在對其他項目的評分中,職員對經理的評分要高於他們對自身群體(職員)的評分。
人們會發現,很難透過表面現象辨別社會角色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人的行為,即使社會角色是隨機分配且特權群體的角色都特別明顯的時候。當然,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是如何完成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事就更難清楚理解了。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分清楚哪些行為是社會角色使然,而哪些行為是源自人的內在性格因素。
在看過了以上這些實驗後,我才明白為什麼我總對我的同事在博士資格口試中提出的機敏問題印象深刻——而通常或多或少會對我的學生給出的不那麼有力的回答感到失望。
基本歸因謬誤常常會讓我們陷入麻煩當中。我們相信了那些本不該相信的人,我們離開了那些其實各方面都很優秀的人,我們僱用了那些一點兒也不稱職的人——所有這些都是因為我們沒能意識到情境性因素的影響力,而它們的確在左右我們的行為。我們會認為人未來的行為能夠反映出我們從他當前的行為中推測出的特點。(所以,你不會想到這種判斷與「過去的行為是未來行為的最好指南」的論斷是不相符的,相反,一個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各種情境之下的行為,才是最佳的判斷依據。在極少數情境下觀察到的行為,尤其是在極少數同類型的情境下觀察到的行為不大有說服力。)
分道揚鑣的人生路
你能達到的水平是和你在一起時間最多的5個人的平均水平。
——吉米·羅恩,美國企業家、勵志演說家
在兒子15歲時,有一天,我碰巧從辦公室的窗口看到他和另一個男孩步行穿過停車場。他們倆當時正抽著煙,而這是我妻子和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不可能這麼做。當天晚上,我對我的兒子說:「今天,我看到你抽煙了,感到很失望。」「是的,我抽煙了,」他挑釁式地回答我,「但這並不是因為同輩壓力。」
而實際上,正是因為同輩壓力。無論如何,他抽煙,正是因為他的同伴中有很多人都抽煙。我們總是因為別人做一些事情而去效仿。他人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並且常常或直接或笑而不語地鼓勵我們模仿他們。他們的成功超乎我們的想像。
社會影響力或許是社會心理學所有領域中被研究最多的課題。然而,我們仍然時常忽視社會影響力,不論是我們在觀察他人行為的時候,還是我們試圖向他人解釋自身行為原因的時候。
最早有記錄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是由諾曼·特裡普利特在1898年進行的。他發現一個自行車手在和他人競速的時候會比獨自計時訓練時獲得更多快感。這個現象在之後的一系列實驗中也得到了驗證。人們不僅會在和他人競爭的時候表現得更有活力,甚至在只是有旁觀者的時候都會更有動力。社會促進效應(social facilitation effect)的影響力也存在於狗、負鼠、犰狳、青蛙和魚類的身上。
(你可能會好奇蟑螂身上是否也存在這種效應。是的,存在!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扎榮茨打開燈,讓蟑螂畏光逃跑。一隻蟑螂會在有另一隻蟑螂緊跟著它的時候跑得更快。蟑螂甚至會在旁邊僅僅有其他蟑螂看著的時候就跑得更快,更何況是當旁觀的蟑螂在搭建起來的看台上時。)
很多年前,我買了一輛薩博汽車,然而不久後便發現我有好幾個同事都在開薩博汽車。後來,我的妻子和我開始打網球,隨後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的許多朋友和親戚也都開始打網球。幾年之後,我們對網球的熱情漸漸褪去。同時,我也發現過去常去的網球場已不復當日人們排隊入場的盛景,已然是空蕩蕩的了。我們去玩越野滑雪,同時期,我的幾個朋友也很熱衷。同樣地,當我們最終對滑雪失去興趣時,我竟然發現曾經那些熱愛滑雪的朋友中的大多數人也差不多放棄了這一愛好。我也不怕告訴你,在諸如餐後小酌一杯、熱衷小型貨車、去看晦澀難懂的藝術電影等事情上都存在這個現象。
我仍不甚明白究竟是什麼因素讓我的朋友、鄰居影響了我和妻子的行為。但是,我可以說,當時《消費者報告》對薩博汽車給出的好評是我們決定買一輛薩博的主要原因。我和妻子想進行定期鍛煉,而家附近恰好有一個網球場,所以似乎自然而然地,我們就去打網球了。總是有另外一些事情,而不是熟人的影響力,可以被歸為我們做一些事情的原因。
我們需要謹慎選擇自己要交往的人,因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會受他們影響。這對於年輕人而言尤甚:你越年輕,受到同伴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便越大。對於一位家長而言,他最重要和最具挑戰性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確保自己孩子的同伴會對自家孩子有好的影響。
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和丹·萊維調查了一些大一隨機分配室友的學生們的平均績點。研究者調查了所有學生在高中時期對酒的消費情況。結果發現,那些高中時的室友有持續飲酒歷史的學生的績點要比高中室友滴酒不沾的學生的績點低0.25。兩者的績點可能分別是B+和A–,或是C+和B–。如果這個學生本身在中學時就是飲酒者,那麼他的績點會比那種自己不飲酒但室友在高中飲酒的學生低整整1。這個差距意味著一個人可以上一所很好的醫學院,而另一個人根本進不了醫學院。(我在這裡有意使用了「他」,因為對於一個女學生,是否有一個飲酒的室友對其並無影響。)
不過,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個對室友不怎麼懷疑的學生不大會把室友飲酒看作自己糟糕的學術成績的主要原因。確實,研究者自己也無法確切地知道室友的行為為何如此重要,因為也許室友飲酒只是一種自然的消遣方式而已。當然,如果你喝酒時間越長,學習的時間就越短,你在學習時的效率也越低。
順便提一句,你也可以簡單地告訴學生們飲酒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學業,而期望喝酒的大學生人數在減少。但這可能並不能打消學生們要與自己的同伴打成一片的想法。
我知道為什麼(奧巴馬總統)想讓你上大學。他想以他的形象為藍本重新打造你。
——參議員裡克·桑托勒姆,在其2012年總統競選活動期間如是說
桑托勒姆參議員關於大學對人的作用的論斷是正確的嗎?這會真正把人們推向奧巴馬總統的政治陣營嗎?
是的,這話起了作用。經濟學家艾米·劉和她的同事對來自148所社區學院和大學(包括規模較大和較小的,公立和私立的,有宗教傳統和非宗教性質的學校)的學生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發現,那些在大學即將畢業時標定自己為自由主義者或極「左」派的人數比新生中如此自評的人增加了32%。而認為自己是保守主義者或極右派的人在即將畢業的學生中的人數則下降了28%。學生們在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婚姻、墮胎、廢除死刑、增收財產稅等問題上的態度逐漸「左」傾。如果有更少的人進入大學,那麼共和黨可能贏得更多的選票。
看起來你也可能在大學裡變得「左」傾。如果是這樣,那似乎是因為你的教授們的自由主義思想要對此負責嗎?你想聽取那些有威望的高年級學生的觀點嗎?我打賭這不會發生。對我而言,我在大學期間變得更加「左」傾,並不是像海綿一樣吸取了教授們的觀點或盲目地跟從我的同學們,我有新觀點是因為我自己對社會本質以及促進其發展的各類事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當然,我在政治觀點上逐漸「左」傾也的確與我從同伴和教授們那裡受到的社會性影響有極大關係。那些教授們不僅對自己的學生影響深遠,他們也會彼此影響。一個保守派學生組織宣稱,聯邦選舉委員會公開的統計數據表明,2012年,常春籐大學的教授中有96%的人為奧巴馬總統進行了政治捐款。委員會還特別指出有一位布朗大學的教授給米特·羅姆尼捐了款。(而這有可能是因為純粹的固執,而不是他的政治立場!)
以上所述的政治捐獻傾向或許比較誇張,但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和曾經的常春籐盟校的教授,我可以向你保證,那些教授的確是極其「左」傾的,而且並未意識到從眾的壓力已經影響到了自己的立場。對於他們自己的生活,那96%的常春籐盟校的教授倒是不會報告說他們認為每天刷牙是個好主意。
其他一些機構也是自由主義的溫床。一位試圖從谷歌公司招募工程師的共和黨人發現,比起公開支持共和黨,人們更有可能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
毋庸置疑,一些機構團體在讓人們形成和加強保守主義立場方面做得同樣成功。在我眼裡,這其中就包括鮑勃·瓊斯大學和達拉斯商會。
當然,美國人不會連續12代人都大規模地轉向「左」派。從那些自由意識強的大學畢業的學生會重新進入一個存在廣泛多樣觀點的世界,而這種環境又會開始影響他們,一般而言會通過一種更加右傾的方式。
並不是只有態度和意識形態才會受到他人的影響。在和一個人談話的過程中,你會不時有意識地改變你的體態。雙臂交疊保持一會兒,把身體重心放在一邊,把一隻手放在口袋裡。看著和你交談的人變換的每一個姿勢,並竭力忍住不笑出聲來。「意念行動模仿」(ideomotor mimicry)是我們無意識進入的一種狀態。當人們沒有進行這種模仿時,交談的另一方會感覺到尷尬和不安。但是,參與者並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問題。換句話說:「他真是個冷冰冰的人」;或是「我們並沒有太多共同點」。
社會影響力無處不在
社會心理學家喬治·吉奧索和理查德·萊克曼做出一項有關社會影響力的開創性研究,他們之前也不曾預料到這項研究會帶來令人欣喜的發現。他們詢問了一群白人高中生對於大量社會議題的觀點,包括一個當時在這些學生所處的社區中十分突出而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即為促進種族融合而開設的校車接送服務。幾周後,調查者召集了那些學生,讓他們對校車接送服務進行討論。每個小組都有4個人,而小組中總會有3個人的觀點相似——他們都對此表示支持,或者都反對。每個組中的第4個人是由調查者有意安排的「搗亂者」,他會準備好一大堆與其他組員相反的觀點去說服他們。討論結束後,實驗對像又填寫了另一份與先前格式不同的問卷,其中有一個問題是詢問他們對於校車問題的看法。
最初反對提供校車服務的學生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看法,轉而支持這項服務。大多數原先支持此計劃的學生則開始反對。研究者要求實驗對像們盡力回想他們對校車計劃的最初的觀點究竟是什麼。但在開始前,研究者提醒學生們他們最初的觀點已經被記錄下來了,然後會借此檢驗學生們回憶的準確性。結果發現,那些被要求參與討論的學生在回憶自己最初的觀點時有比較高的準確性。但是,在參與小組討論的成員中,那些最初反對校車計劃的參與者在「回想」他們先前的觀點時,認為自己支持這一計劃的程度比他們實際支持的程度要高。而最初支持的參與者在回想自己當初的想法時,得出的基本觀點竟然是,他們反對這一計劃!
除了揭示出社會影響力的巨大作用和我們對其的忽視之外,吉奧索和萊克曼的研究還得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重要觀點,即我們對許多事物(包括對一些極其重要的事物)的態度不是來自某個「思維檔案庫」,而是在遇事時即刻形成的。就像人的觀點會轉向一樣,我們對自己過去想法的印象也常常是「編造」出來的。2007年,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會給任何一個共和黨的候選人投票,而不會投票給當時人氣頗高卻沒經過什麼歷練的奧巴馬。2008年,當他狂熱地要給奧巴馬投票之前,我向他提起了那件往事,他十分生氣,還認為那一定是我捏造的故事。我自己也常常會被別人提醒,現在我強烈支持的某種觀點和我過去的想法是矛盾的。每到這種時候,我總是覺得真難想像這個曾經表達過那種觀點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評估行為動因時的「行動者-觀察者」差異
幾年前,和我共事的一名研究生告訴我一件關於他自己的事,讓我驚詫不已。他曾因為謀殺而入獄。他並沒有直接殺人,只是因為他的熟人犯案時他在場,檢方便因此以協同謀殺而起訴了他。
我的這個學生又告訴了我一件關於他的謀殺犯獄友的事,著實令人震驚。殺人者總會把兇案發生歸咎於他們所處的環境。「我讓櫃檯後的那個傢伙把所有的錢都交出來,他卻躲進了櫃檯底下。這樣我就不得不拿刀捅向他。我對此感覺糟透了。」
這一類的歸因背後明顯有為自己辯護的動機。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因此而明白,人們通常會認為他們自己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所處環境的一種理智的回應——無論這種行為是善行還是可鄙。然而,我們很難認可他人行動中的情境因素的影響,所以我們更有可能在評判他人時犯下基本歸因謬誤——將個人性格因素看作其行為最主要或唯一的動因。
如果你問一個年輕人,為何要與某一個女孩約會,他可能會回答「她是個十分溫暖的人」。如果你問同一個年輕人,他的一個朋友為何要與某一個女孩約會,他則可能回答說「因為他需要一個沒什麼壓力的女朋友」。
當你問一個人,他們的行為,或者他們最好朋友的行為通常是會反映出他們的個性,還是他們的行為主要受環境影響,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朋友的行為在不同場景下有高度的一致性,且一致程度比他們自己要高。
行動者與觀察者對行為歸因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情境對於行動者而言更明顯。我需要知道我所處情境中的重要信息,這樣我才能夠做出恰當的反應(雖然我肯定會有意丟開或忽視一些重要信息)。但是,你並不需要對我所面對的情境給予特別細緻的關注。相反,對你而言,最明顯的是我的行為。因此,你很容易從描述我的行為(好或劣)轉而描述我的個性(善良或殘酷)。你常看不到,或可能會忽略,我所在的情境中的重要因素。無論如何都無法避免你在評價我的行為時將其歸因於我的個性。
文化、情境和基本歸因謬誤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人會高度關注自身的狀況。他們往往專注於追求自身的興趣所在,較少關注他人關心的事物,而在許多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則會在自己的生活中受到很多限制。西方人的這種自由始於古希臘人推崇的一種極強烈的個體主導。相較而言,同樣古老而發達的中國文明則更多地強調群體的和諧之感,而不是個人行為的自由。在中國,有效的行為總會要求與他人順利地合作,無論是與上級還是同伴。直到今天,西方文明中的獨立自主與東方文明中的相互依存之間的差異依然明顯。
在《思維的版圖》[1]一書中,我曾指出,東西方這種不同的社會文明根植於其相異的經濟源起。希臘人的生計維繫在相對獨立的職業類型上,比如經商、捕魚、畜牧養殖,在農耕上有家庭菜園、橄欖樹種植。中國人的生計主要就維繫在農業種植上,尤其是種植稻米,這項工作對合作的要求更高。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無法獨立完成一項工作,那麼治理這個社會最有效的方式或許就是專制統治(統治者大多會表現出仁慈,但有時不會)。
所以,對中國人而言,關注社會情境是必要的,但對希臘人而言則不是。這些在關注點上的差別已經通過各類實驗得到證實,實驗者有來自西方的希臘獨立傳統繼承者,也有東方中國儒家傳統的傳承者。我最喜歡的一個實驗是由日本的社會心理學家益田孝彥設計的。他讓日本和美國的大學生對下面這幅漫畫中位於中間的那個人物的表情進行評價。

日本學生的描述是,當畫面中間的人被四周悲傷的人(或是生氣的人)包圍時,會比他被快樂的人包圍時顯得悲傷。而美國大學生對畫面中間那個人物的評價則不太受到他周圍人物表情的影響。(這個實驗還以其他形式進行過,即畫面中間的人物的表情是悲傷的或者生氣的,而周圍的人則是快樂的、悲傷的或生氣的,得出的結果相似。)
人對情境的關注也體現在物理環境上。如果想看一下人們對以人為背景的情境和以物為背景的情境的關注有多大的差異,請看下面這個從一段時長20秒鐘的彩色視頻中截取的場景,它表現的是水下的畫面。益田和我向很多人展示了這段視頻,然後讓他們描述看到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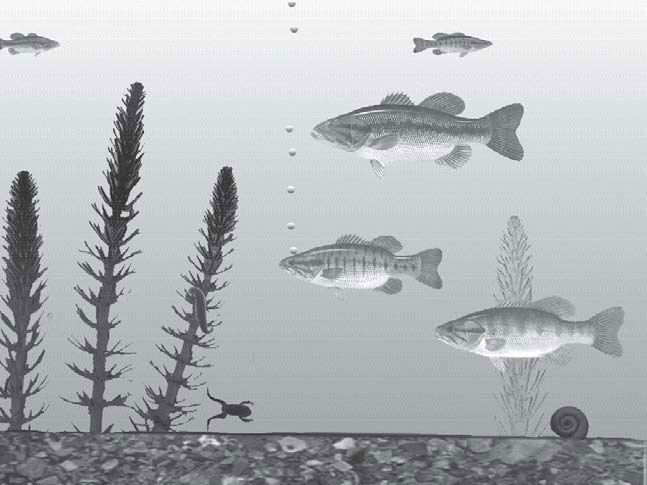
美國人一般這樣開始敘述:「我看到了三條大魚向左邊游,它們有粉紅色的鰭,白色的腹部,背上有垂直的條紋。」日本人則更可能會這麼說:「我看到了一條溪流,水是綠色的,在溪流的底部有岩石和貝殼,有三條大魚向左邊游。」只有當把情境搭建起來之後,日本人的焦點才會集中到對美國人而言最明顯的事物上。總體而言,日本人報告自己看到背景事物的比例比美國人高60%。這就是你能預想到的,東亞文化背景下的人會比西方人更關注情境。
這種對情境性因素不同的關注點使得東方人在對人的行為進行歸因時,更傾向於情境性解釋,而西方人則更可能將行為動因歸結於個人性格。韓國社會心理學家的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你告訴一個人,某個人在一個場景中的行為與大多數人的表現一樣,那麼韓國人會相當肯定地推斷,某種情境性因素是導致人們行為的主要因素。但是,美國人會認為是個人的性格因素引導了他的行為——而忽略其他人在情境中會有同樣的行為。
東方人容易受到基本歸因謬誤的影響,但不會像西方人那麼明顯。比如,一個和瓊斯與哈里斯所做的實驗相似的實驗表明,人們傾向於認為,一篇論文作者的觀點與文章本身的觀點是契合的。崔仁哲和他的同事證明了,來自韓國的實驗對象也會犯和美國人同樣的錯誤。研究者提供給這些實驗對象的情境類似於那個要求人們讀論文的情境,韓國人抓住了重點,但並不認為作者的真實態度就是反映在文章中的態度。美國人則不會從明顯的情境中獲取什麼信息,而是從作者的觀點中得出結論。
東方人傾向於對這個世界抱有一種整體性的觀點。他們將事物(包括人)放在情境中來看,因此更願意把行為成因歸於情境性因素,他們密切關注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西方人則有更具解析性的思維。他們關注事物,注意它們的特質,按其特質分類,然後會以這一類事物所具有的標準來看待某個具體的事物。
這兩種思維方式都有其合理性。我毫不懷疑,解析性的思維方式在西方人占主導的科學世界裡扮演了重要角色。科學的基礎即是對事物進行分類,以及探究不同類別的事物所遵循的法則。事實上,當中國文明萌發生長之時,希臘人也發展出了自己的科學,雖然在數學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但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體系。
但是,整體性思維幫助東方人避免了在理解他人行為時會犯的嚴重錯誤。此外,那種不情願將行為原因歸於人的個性的心態幫助東方人建立了一種信念,即人有能力做出改變。正如我們將在第14章中看到的那樣,在辯證思維方面,認為人的行為具有可變性的想法讓東方人對一些重要問題做出了正確判斷,而西方式的思維則常犯錯誤。
小結
在前兩章中我們學到的重要一課是,我們的思維過程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這項關於日常生活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複雜且深刻。
關注情境。這會讓你更準確地辨識影響你自己和他人行為的情境性因素。具體而言,關注情境會幫助你識別出有效的社會影響力,反思可能無法讓你明白對你的思考過程和行為造成影響的社會情境因素。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社會影響力因素對他人的作用,那麼其實肯定你也會受到它們的影響。
意識到情境性因素通常會比它們看上去更深刻地影響你和他人的行為,而個性因素通常比它們看上去的影響力要小。不要以為,通過某個人在一個或兩個情境中的行為就能夠預測其未來的行為。也不要認為,一個人所擁有的個性、信仰或偏好導致了他的行為。
意識到他人對自己行為的歸因會更偏於情境性因素,而你更願意將他人的行為動因歸結於其個性因素——他們其實比你更正確。他們對自己所處的情境(以及自己的過往)瞭解得更全面,比你知道得更清楚。
承認人會改變。自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方人一直相信,世界是恆定的,各種事物,包括人,都會依照他們固有的個體特徵而行事。東亞文化背景下的人則堅信,變化才是唯一的恆常之事。改變環境,就會改變一個人。後面的章節中會論述,變化的世界觀通常會比恆常的世界觀更正確,也更有用。
上述建議會成為你思維工具的一部分,幫助你理解這個世界。這些工具中的任何一種,你使用一次就會有更多的應用機會,因為你會看到它們的實用性,而同時你還會發現可以在越來越多的情境中應用這些思維的工具。
[1]《思維的版圖》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06年2月出版。——編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