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髮生黑絲
大歷四年的冬天,寒流侵襲潭州(長沙),大雪下得家家灶冷,戶戶衣單。杜甫以船為家,停泊在湘江岸旁,從秋到冬,已經四個多月了。左右鄰船,都是捕魚為業的人。漁夫們最初看杜甫是個外鄉人,不知他是幹什麼的,對他懷有戒心。後來看這滿頭白髮的老人,右臂偏枯,兩眼昏花,帶著一家人,生活和他們一樣貧困,日子久了,就不把他當外人了。他們有時從漁市上回來,提著半罐酒到杜甫的船上閒談,杜甫有時也到他們的船上坐一坐。彼此熟了,大家無話不談。談來談去,總要談到漁稅上邊來。天寒水淺,大魚都入了洞庭湖,漁網又常常凍得撒不開,可是官家的漁稅總是有增無已。越逼近歲暮,魚越少,稅吏的面孔就變得更為獰惡。這真叫人活不下去。一個年老的漁夫憤慨地說,“從我十幾歲扯起漁網的那天起,漁稅就壓在我的身上,好像打魚就是為了交漁稅。打了一輩子的魚,交了一輩子交不清的稅。索性天下的水都干了,魚都死光,打魚的人都沒有了,倒也痛快!”老漁夫抬起頭來,望一望船篷外茫茫的大雪,接著說,“叫他們向這冰天雪地要漁稅吧!”
聽著這類的話,杜甫暗自思忖,十幾年來,東奔西走,總看見農民身上背著一輩子交不清的賦稅。男人死了或是逃亡了,女人還得交稅;錢和糧都光了,差吏就把衣服和用具拿去抵償;衣服和用具拿完了,還交不清稅,只好賣兒鬻女。如今他五十八歲了,陸地上沒有一塊安足的地方,滯留在這條狹窄的江上,摻雜在過去很少接觸到的漁民中間,想不到這裡的人也被租稅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回想今年春天,初入潭州,停泊在花石戍,登岸散步,但見田園荒蕪,柴扉空閉,農具仍在,農民卻逃亡得無影無蹤。這帶地方並沒有遭受過北方那樣的兵燹,竟也這樣萬戶蕭條!這是沉重的賦稅造成的後果。他心裡納悶,當今的皇帝怎麼這樣不察民情,於是脫口吟了兩句詩,“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現在看來,下令減稅是不大可能的,湘江的水是不會幹的,魚也不會死光,但是漁民走投無路,把漁網拋在江裡,像農民一樣逃亡在外,另謀出路的日子恐怕也快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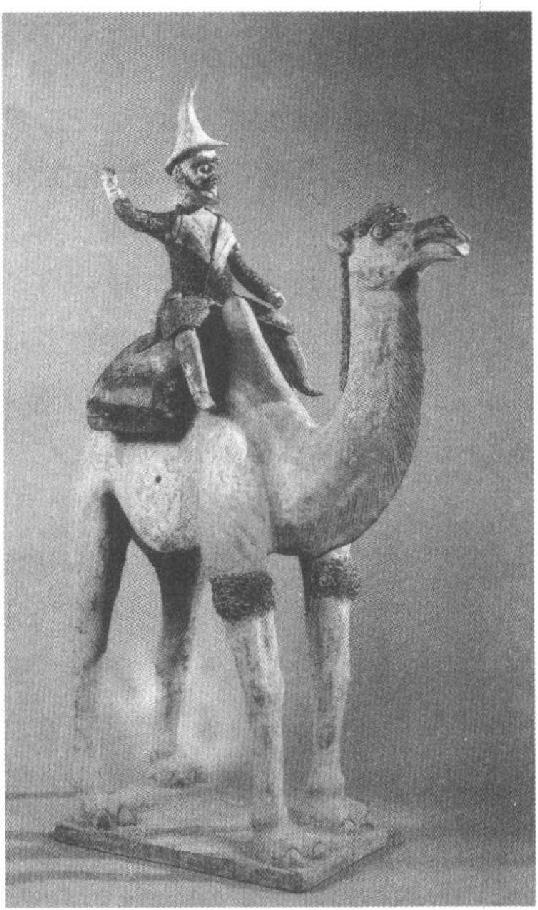
漁夫們說完自己的苦楚,看見杜老(他們這樣稱呼他)的生活比他們更可憐。他雖然沒有租稅負擔,卻是老病纏身,衣食無著,楊氏夫人常常眉頭雙皺,凝視著滾滾不息的江水,愁著沒有米下鍋。十六歲的兒子宗武餓得滿臉蒼白,每天還要用很多的時間讀什麼《文選》。漁夫們私下裡常常為杜甫的生活擔憂,覺得這一家人飄流在外,無親無友,總要有點打算才好。這天大雪不住地下,老漁夫傾吐了滿腔的憤慨,看見杜甫穿著一身單薄的衣裳,到處是補丁,凍得直是咳嗽,不禁轉換了笑顏,把他暗自為杜甫盤算了許久的一個辦法說了出來。他說,“杜老,請你不要見怪,你的生活也實在艱難。我有一個主意,不知你肯聽不肯聽?上月我患風濕病,骨節酸痛,四肢發麻,你給了我一包蜀地的蒼耳,我熬水喝了幾次,很見好轉。還有你從北方帶來的決明子,也治好過船上孩子們的眼病。杜老,你有這樣的靈藥,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到魚市上擺個藥攤賣藥呢?既可以醫治病人,又可以買點米回來。”漁夫說完了,有點擔心杜甫見怪,於是補充了一句,“不知杜老覺得怎樣?”
杜甫認真地聽完了這段話。在老漁夫為杜甫出主意的同時,杜甫的心裡就在想,賣藥,我是有經驗的,在長安時,我在王公貴族的府邸裡賣過藥,在成都時,我在一些官吏中間賣過藥,如今流落潭州,為什麼不能把藥賣給老百姓呢?他沒有等漁夫補充的那句話說完,就把漁夫前邊的話重複了一遍,“既可以醫治病人,又可以買點米回來”。這表示他接受了漁夫的建議。
大雪過後,刮了兩天刺骨的冷風,把陰雲吹散,氣候漸漸轉暖。楊氏夫人從箱籠裡找出來一包一包的草藥。這些多年的草藥,有的是從前自己培種的,有的是從山野裡採擷的,其中還有少許在同谷縣深山裡挖掘的黃獨。十幾年的積累,經過自己的服用和分贈朋友與路人,剩下的也還不少。楊氏夫人把藥分門別類,裝在一個布袋裡,交給杜甫,杜甫拿在手裡,並不覺得怎麼重。
在一個比較和暖的早晨,杜甫跟著左右鄰近的漁夫到了離這裡不很遠的魚市。
杜甫聽從了老漁夫的勸告,眾漁夫覺得像是聽從了他們共同的勸告一般,都喜笑顏開。魚簍裡的魚本來就不多,而且又都是小魚,他們心裡明白,反正賣不了多少錢,今天與其說是賣魚,倒不如說是幫助杜甫賣藥。大家希望杜甫賣藥一開始就能得到成功。他們把魚市上最優越的地位讓給杜甫擺藥攤,那是一座廟台,又干松,又引人注意,有主顧來買魚,漁夫們並不誇獎自己的魚是怎樣新鮮,卻都指著廟台上的藥攤,說那些藥如何珍貴,都來自產藥聞名的地方,有長安的,有隴西的,有成都的,有夔州的,其中有些藥在潭州花多少錢也買不到。沒有多久,賣藥的事就傳遍了魚市的周圍。附近長期患風濕病的、打擺子的、鬧眼病的……都爭先恐後,到藥攤前來買藥。價廉物美,不到一上午,杜甫的藥賣出不少。
市集過後,漁夫們圍攏著杜甫,回到船上,把杜甫賣藥成功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大家有說有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杜甫和他們的交誼也更深了一層。
此後每逢市集,只要天氣不太壞,杜甫就跟著漁夫們到魚市上擺藥攤。買賣進行很順利。楊氏夫人也暫時展開了愁眉,不只有錢買米,而且還間或能給杜甫置辦一點酒肉。宗武的面色好像也不那麼蒼白了。這中間,老漁夫卻又有一點另外的擔憂。他知道,杜甫的藥是舊日的儲存,沒有新的來源。賣完了舊存,沒有新貨,固然嚴重,更嚴重的是杜甫身體衰弱,一旦舊病發作,這可怎麼辦。又看他整個上午坐在廟台上招呼買主,也太辛苦了。他於是囑咐年輕的漁夫們,此後不要過分為杜甫的藥吹噓;每逢看到杜甫賣出一點藥,夠買幾斤米時,就催促他早點收攤回家。
後來老漁夫想出來一個望長久遠的辦法。他取得楊氏夫人的同意,帶著宗武到遠方藥市上置辦一點新的藥材,放在杜甫的藥袋裡,把杜甫經常服用有效的舊藥取出,交給楊氏夫人好好保存。一遇到杜甫顯出有些疲倦的樣子,他就說,“杜老,你在船上休息吧,叫宗武跟我們去擺藥攤,這孩子也是懂得藥性的。”老漁夫對杜甫的關懷,使杜甫深受感動,他又聽從了老漁夫的話,此後就常常讓宗武替他去賣藥。
一天,宗武又和漁夫們一起到魚市上去了。陽光照耀著水上的波紋,江上的船隻輕輕地搖來搖去。楊氏夫人把船板刷洗得乾乾淨淨,杜甫一人靠著長年隨身的烏皮幾,心情平靜,不由地想起許多問題。
他一生飽經憂患,用盡心血,寫了兩千多首詩,詩裡描述了民間的痛苦、時代的艱虞和山川的秀麗,而莽莽乾坤,自己卻漂泊無依有如水上的一片浮萍。自從中年以後,衣食成了問題,誰像這些漁夫那樣關心過他?從前在長安時,是“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如今在達官貴人面前,仍舊是“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日暮途窮,真像是可憐的“窮轍鮒”和“喪家狗”。多少親朋故舊,以及一些作詩的朋友,見面時輸心道故,甚至慷慨悲歌,可是一分手就各自東西,誰也照顧不了誰。想不到兒個萍水相逢的漁夫,對他卻這樣體貼照顧,無微不至,使他感到無限溫暖。而自己過去對待窮苦的人是怎樣呢?回想兩年前在夔州,生活比較安定,家裡有一棵棗樹,任憑西鄰一個無食無兒的婦人過來打棗兒食,不加防止,秋收時,地裡多丟下一些谷穗,任憑村童拾取,也不干涉,自以為這就是很能體貼窮人了。此外寫了些替窮人說話、為窮人著想的詩歌,但是比起漁夫們對他的熱心關懷,還是差得很多。像在成都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是出自一片至誠,但是對於無處棲身的“寒士”們到底能有什麼真正的幫助呢?想來想去,總覺得自己愛人民的心遠遠趕不上漁夫們愛他的心那樣樸素,真誠,而又實際。他看見農民和漁民被租稅壓得活不下去時,想的只是“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可是漁夫們看見他活不下去時,卻替他想出具體的辦法。請皇帝減徵賦,只是一個空的願望,而漁夫替他想的辦法,卻立見功效。
他對於那兩句自以為很得意的詩發生了疑問。
正在這時,宗武提著藥袋回來了,後邊跟著一個客人。
這客人大約四十多歲,中等身材,矯健精悍,目光炯炯。上了船,和杜甫寒暄了幾句,聽出來是山南巴州人的口音。他說他姓蘇名渙,是潭州刺史崔瓘幕府裡的從事。
蘇渙這個名字,杜甫在閬州、梓州時,彷彿聽人提到過。人們說他是一個精良的弩手,百發百中,在巴山道上常常搶劫顯官富賈,綽號人稱“弩跖”。州府裡說他是個出沒無常的強盜,田野間說他是個殺富濟貧的俠士。不知怎麼回事,不久又中了廣德二年的進士,充任侍御使。後來,杜甫回到成都,轉徙夔州,關於蘇渙這個傳說紛紜的人物,也就很少聽人提到了。今天出乎意外,他出現在杜甫面前,杜甫感到無限驚奇。
蘇渙卻一見如故,無話不談,沒有絲毫避忌。這時江上風和日暖,好像大地將要回春,楊氏夫人烹茶煮酒,款待這稀有的客人。客人說,過去在巴州的故鄉,就仰慕杜甫的大名,杜甫的詩卻讀得很少。最近在崔刺史幕府裡的書案上讀到幾卷傳鈔的杜甫的詩,其中有《石壕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那樣的名篇,有“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那樣的警句,有“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盜賊本王臣”那樣的至理名言,真感到不同凡響,這是陶潛死後三百年來難於聽到的聲音。能夠與這樣的詩的作者生逢同時,是一件大快事。最近潭州居民都互相傳告,魚市上有位賣藥的叫作杜甫,所以特來拜見。“你老人家可就是這些詩的作者?”說到這裡,蘇渙的語調轉為低沉,杜甫的心裡也勾起一縷淒涼的情緒。
他沒有等杜甫回答,就接著說起他自己的過去。“你老人家在閬州時,也許聽人說過巴州有我這樣一個強盜。我們巴州一帶的 〔1〕人,從來就剽勇善戰,又能勤勞生產,織出的布匹天下聞名。這些布匹雖不輕柔華麗,卻是堅固耐久。劉邦和項羽爭天下的時候,劉邦聽取了閬中敗類范目的獻計,徵募
〔1〕人,從來就剽勇善戰,又能勤勞生產,織出的布匹天下聞名。這些布匹雖不輕柔華麗,卻是堅固耐久。劉邦和項羽爭天下的時候,劉邦聽取了閬中敗類范目的獻計,徵募 人為他平定三秦。此後
人為他平定三秦。此後 人的命運便算注定了,供歷代帝王牛馬一般地驅使。一有戰事,就徵調
人的命運便算注定了,供歷代帝王牛馬一般地驅使。一有戰事,就徵調 人為他們打仗;戰事平定了,又向他們征斂大批的布匹。
人為他們打仗;戰事平定了,又向他們征斂大批的布匹。 人的布匹永遠織不完,自己的身上穿的卻永遠是破破爛爛。十幾年來,外地的商人也看上
人的布匹永遠織不完,自己的身上穿的卻永遠是破破爛爛。十幾年來,外地的商人也看上 布了,他們運來一點米、一點鹽,用一本萬利的鹽米,向他們騙取大量的布匹。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變,自稱梁王,也到巴州來募兵。我親眼看著
布了,他們運來一點米、一點鹽,用一本萬利的鹽米,向他們騙取大量的布匹。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叛變,自稱梁王,也到巴州來募兵。我親眼看著 人世世代代無法擺脫的負擔和痛苦,我不能容忍了,我說,來個結束吧。我糾集了百十個健壯的青年,隱伏在巴山裡,仰仗著我的弩弓,專門劫殺吸血的商人和敲人骨髓的官吏。”說到這裡,他臉上露出一點笑容,好像要緩和一下由他的談話所引起的緊張氣氛。他笑著向杜甫說,“你的《光祿阪行》裡有兩句詩,‘馬驚不憂探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請你放心,那時你若是從我們巴州的山下經過,我們的長弓是不會向你射擊的,我們會對你表示熱烈的歡迎。”
人世世代代無法擺脫的負擔和痛苦,我不能容忍了,我說,來個結束吧。我糾集了百十個健壯的青年,隱伏在巴山裡,仰仗著我的弩弓,專門劫殺吸血的商人和敲人骨髓的官吏。”說到這裡,他臉上露出一點笑容,好像要緩和一下由他的談話所引起的緊張氣氛。他笑著向杜甫說,“你的《光祿阪行》裡有兩句詩,‘馬驚不憂探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請你放心,那時你若是從我們巴州的山下經過,我們的長弓是不會向你射擊的,我們會對你表示熱烈的歡迎。”
這句開玩笑似的話把杜甫也說笑了。初次見面,就這樣沒有分寸,話剛脫口,蘇渙就自覺失言,可是杜甫並不介意。蘇渙立刻接著說,“你在梓州、閬州時期的詩,還是‘盜賊本王臣’說得對。那些王公大人說起強盜來,像是說一種怪物,罪大惡極,個個該殺,其實強盜哪一個不是善良的老百姓?租稅徭役,逼得人們無路可走,不起來當強盜又怎麼辦?不過你老人家還是太忠厚了一些,總希望皇帝略有醒悟,能減稅減租,來解除他們的苦難,你看,這能辦得到嗎?皇帝和他的大臣們,若是不向老百姓索取租稅,還不是比窮人更沒有法子活下去?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織布,三不會打魚……不過我當時也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以為自己有一片好心腸,有一套好武藝,只要振臂一呼,就可以解除大家的苦難。實際上,我們起事不久,就因為人力孤單,遭到了失敗。”
他沒有說他是怎樣失敗的,杜甫也不想追問。杜甫近來常常考慮,到底怎麼樣才能真正解除百姓的苦難,想來想去,總是想不通,現在聽到蘇渙這一番話,像是聞所未聞,卻也含有一些新的道理。這道理彷彿是在八表同昏的宇宙中透露的一線微光,在處處窮途的旅人面前伸出來的一條小路。但他一時回答不出話來。
蘇渙從懷裡取出一個小手卷。他一邊打開手卷,一邊說,他本來不慣寫詩,近些年來,有了不少感觸,還是用詩寫下來比較合適,因此寫了許多首,可是不大講究格律,現在吟誦幾首,請杜甫指教。他用沉重的語調把下邊這首詩讀給杜甫聽:
毒蜂成一窠,高掛惡木枝;
行人百步外,目斷魂亦飛。
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
右手持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
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
徒有疾噁心,奈何不知幾。
杜甫一聽這首詩,就知道是蘇渙從個人失敗中得到的教訓。詩在藝術上,若拿杜甫平素對詩的要求來衡量,是相當粗糙的。但是它蘊藏著一種新的內容,表現了一種新的風格。杜甫把這首詩吟味了片刻,便興奮地向他說,“我一向稱讚陳子昂的《感遇詩》、李白的《古風》,今天聽到你讀了這首詩,可以說是陳李以外,又樹立了一個新的旗幟。‘徒有疾噁心,奈何不知幾’是你作了一番事業以後,得到的經驗。我也一向疾惡如仇,可是從中取得這類經驗的事業,不用說做,我連想都還很少想過呢。”

蘇渙聽了杜甫對他的讚許,十分高興,聽到最後一句杜甫自己的感慨,他只認為是杜甫的謙虛。他被讚許所鼓舞,接著又誦讀了幾首。詩的體裁是一致的,內容比前邊的那首更豐富了,涉及到日月的運行和宇宙的變化,世路的艱險和統治者的殘暴,人民的痛苦和必然的反抗……讀到最激昂的地方,詩裡才思雲湧,辭句動人,每逢一首讀完了,都像有些東西沉重地壓在人的心上。小小的船篷裡,任憑日影移動,“書篋幾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
鄰船上一片人聲,漁夫們從魚市上回來了。蘇渙誦詩也戛然停止。他站起身來,和杜甫告辭,並約杜甫有工夫到他的茅齋裡去談。
杜甫吃過午飯,精神異常興奮。午睡不成,只是反覆吟味著蘇渙讀給他聽的那些詩。詩的功夫並不深,但格調與眾不同。李白早已死去了,高適也死了,岑參還在西蜀,卻久不通音訊,也沒有聽說他有什麼新作。大歷改元以來,聽人傳述的一些所謂新派的詩人,不是用詩諂媚權貴,就是騙取女人,詩風墮落到這等地步,致使他今年春天在《南征》詩裡寫過這樣的詩句,“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以表達他的寂寞心情。在難以盼望有什麼知音的時刻,竟遇見了這樣一個奇人。
蘇渙所欽佩於杜甫的,是杜甫已經完成的驚人的成就;杜甫所傾倒於蘇渙的,是蘇渙詩裡隱示著許多過去還沒有人道過的新的內容。若是對蘇渙的詩給以評價,可以說是突過了魏文帝黃初時代的詩人們。但是個別的地方,杜甫並不以為然。蘇渙誦讀過的詩中有這樣四句:
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杜甫還記得,賈誼在《論積貯疏》裡引用過古人的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趙曄的《吳越春秋》也有類似的句子。蘇渙的詩顯然是從漢代的這句諺語裡脫化出來的。他把“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寫成“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已經有些誇張了,不過去原意還不遠;但是後兩句為什麼改寫成“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呢?難道一夫不得意,真能使四海行路難嗎?杜甫暗自考慮,這兩句詩若是根據古人的原意,就應寫作“一夫不得耕,萬人難為餐”,若是保留蘇渙的“四海行路難”,那麼“一夫不得意”要改成“眾人不得意”才好,“一夫”反正是不大妥當。
杜甫儘管不能同意蘇渙詩中個別的詩句,但是蘇渙這個人和他的詩的出現,在杜甫看來,確是一個奇跡。同時他又把鄰船上漁夫們的生活、言語、思想、感情認真思索了一番,覺得自己一生漂泊,看見的事物不算不多,接觸的人不算不廣,但究竟世界上還是有許多人和事過去不只沒有遇到過,而且也沒有想到過。不料在這垂暮之年,眼前又湧現出一些新的事物。自己也覺得年輕了許多,好像白頭髮裡又生出黑絲。過去懷念古人,常常有“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慨;如今設想將來,不知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是看不到了。蘇渙說,他能和杜甫生逢同時,是一件快事;杜甫今天能遇到蘇渙,心裡也同樣高興,真好像司馬相如遇見了一百年後的揚雄。他情不自禁,提筆寫出來這樣的詩句: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
再聞湧新作,突過黃初詩。
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
今晨清鏡中,白間生黑絲;
余發喜卻變,勝食齋房芝;
寫到這裡,江上已是黃昏,暮靄蒼茫,兩岸人家疏疏落落地升起幾縷炊煙。一陣寒風乍起,江水拍擊著船身。近些天,杜甫每逢聽到夜半的風聲便感到心神不寧,彷彿古代的神靈在湘江上出沒。杜甫趁天色還沒有完全黑,迅速把他那種感覺凝煉成四句詩,寫在紙上,作為這首詩的結束:
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悲,
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
杜甫和蘇渙很快就成為親密的朋友了。有時蘇渙到杜甫的船上,有時杜甫到蘇渙的茅齋。二人無話不談,彼此也有了更深的瞭解。杜甫看蘇渙有如蟄伏在沙水裡的蛟龍,很惋惜這樣的人材,朝廷不能使用。杜甫常常流露出這種惋惜之情,蘇渙卻是另有一種看法。他說,“我放棄了巴州的強盜生活,並且進士及第,人們說我折節讀書,改邪歸正,但是我並不指望朝廷看中了我。”他指著牆上的弓弩向杜甫笑著說,“我並沒有拋棄這個東西。”
杜甫聽他這樣回答,很難推測他心裡想的是什麼,只覺得他坦率親切,並不是什麼危險人物。兩人的政治態度有相當的距離,卻不是沒有漸漸接近趨於一致的可能。杜甫建議他修改“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那兩句詩,他表示接受,說是考慮考慮再改。杜甫從他那裡也得到不少啟發。杜甫雖然沒有放棄對皇帝的幻想,但是認為指責朝廷不合理的措施,愛護掙扎於生死之間的百姓,應該更為積極。他身體儘管衰弱,百病纏身,精神卻更為健壯起來。他在一首寄給朋友的詩裡寫出“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這樣堅強的詩句,用以表明自己的態度,還把這首詩讀給蘇渙聽。
一天,天晴氣朗,杜甫望著岳麓山想到遠方的南嶽,無意中背誦起建安詩人劉楨的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背誦到第四、第五句“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時,心裡起了一種難以調和的牴觸情緒,再也背不下去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真正的鳳凰絕不會羞與黃雀同群”。他立即把劉楨的詩意反轉過來,寫了一首《朱鳳行》,詩的下半首是,“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從此杜甫終日生活在漁夫們中間,也經常和蘇渙來往。過了元旦,又過了清明,新歸來的燕子好像舊相識似的穿過船篷,兩岸桃李盛開,杜甫兩目昏花,也覺得花枝照眼,生趣盎然,白髮裡的黑絲彷彿又多了一些。在這美好的春光裡,儘管鴟梟般的貪官污吏到處橫行,混亂的局面還沒有止境,他內心裡卻充滿了力量和希望。
忽然在一個四月的夜裡,潭州城內,火光四起,居民奔走相告,說湖南兵馬使臧玢叛變了,刺吏崔瓘已被殺死,士兵們正在大街小巷姦殺搶掠。這突然發生的事變,在湘江上的漁船中也引起一片騷亂。大家不知如何逃避時,蘇渙在人群中出現了,他手裡沒有拿著別的東西,只有一隻弓弩。
他跳到船上,向杜甫和漁夫們說,“大家不要慌亂,我陪送大家暫時躲避一下,有我這只弓弩,看哪個亂兵敢侵犯我們。”
這晚月光皎潔,杜甫的船和漁夫們的船結成一隊,蘇渙手持弓弩站在船頭,逆著江水向南駛去。後來到了衡州,蘇渙看見杜甫和漁夫們脫離了危險,和他們揮淚告別,獨自往嶺南去了。
杜甫雖然又經歷了一次變亂,精神仍然是健壯的。但是這年冬天,忽然百病俱發,不久便病逝在湘江上的船中。蘇渙到了嶺南,東漂西泊,最後參加了循州刺史哥舒晃的起事,又遭受失敗,被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殺害。這時距杜甫逝世,已經過了五年了。
寫於一九六二年春
〔1〕 人——古代四川北部一個少數民族的名稱。
人——古代四川北部一個少數民族的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