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裡,最振聾發聵的一句,莫過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時至如今,很多人已經不以為然,以為今日之中國,不論財力物力、軍力國力,都不復當年的窘境,甚至已經算得上世界強國,雖然我們常自謙地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可沉睡的獅子已然猛醒,我們是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巨人,再也不是被人欺凌的「東亞病夫」。
可是,危機真的過去了嗎?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而相較於因外族侵略引發的亡國之險,因文化衰微而引發的亡種之虞其實更為可慮,也更為可怕。
事實上,20世紀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發的亡國之險爆發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漢字,作為漢民族文化的底線與憑依,其危機已然發端。遠在甲午戰爭戰敗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與批判,到了五四運動,這種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終於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烽火,並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如能客觀地回頭審視,就會發現,新文化運動本身同樣需要反思,筆者以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處,就是新文化運動中欲求「漢字革命」而致「廢滅漢字」的態度。
錢玄同寫於1922年的《注音字母與現代國音》一文交代了這種態度產生的源起。文章說:「1894年,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見,當時知識分子欲求漢字革命的初衷,是認為漢字的書寫認記之難影響了國民普及教育的推廣。在這種想當然的線性邏輯關係中,漢字只是一種純粹的書寫工具,彷彿與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史並無什麼本質的關聯,所以傅斯年在1919年的《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一文裡便斬釘截鐵地說:「文字的作用僅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沒有絲毫作用。」基於這樣的出發點,文章於是有了更為斬釘截鐵的判斷——「中國人知識普及的阻礙物多的很,但是最禍害的,只有兩條:第一是死人的話給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代生活的社會裡。」
這種過猶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認知隨著救亡圖存時代的來臨,因變革圖強之心而變得更為偏激。到了30年代,魯迅在《關於新文字》一文裡甚至把漢字比喻成結核病菌,他說:「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因此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裡斷定說:「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魯迅的知己瞿秋白更是將漢字比喻成「殭屍」,甚至在《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一文中用極端情緒化的語言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茅坑。」
從錢玄同、傅斯年到魯迅、瞿秋白,還有蔡元培、胡適、趙元任等一大批那個時代傑出的知識分子,因為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時代因素裹挾著種種情緒化的認知,他們所推崇的「廢滅漢字」運動曾一度引發了漢字危機。當然,這其中也不乏理性的聲音,聞一多早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就在《論振興國學》一文中明確主張:「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國粹之所憑也。」這是強調一國之文字與一國之文化有著血脈上的本質關聯,甚至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憑依與根本所在。事實上,不論是錢玄同、傅斯年、魯迅、瞿秋白,還是蔡元培、胡適、趙元任,這些仁人志士以筆為鋒,以思想為戰,所著所論,所倡所言,最後不還是要依賴於漢字與漢語的傳達?離開了母語環境,離開了民族的漢字,他們的思想與價值又何從體現?
至於說漢字的難識難認影響了教育的普及,更是一種簡單的假設與推理,事實上,如今教育普及的現狀與漢字依然屹立的現實,就足以說明這種假設是一種想當然的「有罪推定」。以此將某個特殊時代民族文化思想上的落後與故步自封一股腦兒地歸咎於漢字,對於漢字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天大的冤枉。況且,漢字是否就如前人所想的那麼難於書寫認記,還不一定。中央電視台2013年首屆《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092號選手李響悅,年齡不過14週歲,靠著漢字音形義的聯想在比賽中屢屢過關斬將,寫對很多自己此前也未曾接觸的字詞,這充分說明漢字在書寫認記上有著獨特的規律與優勢。無論如何,漢字正是憑藉著自身的生命力,憑藉著它作為「文明之所寄,國粹之所憑」的根本地位,在「廢滅漢字」運動的巨大衝擊中,最終屹立不倒。
新中國成立後,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所及,漢字的危機依然存在。既然要「廢滅漢字」,就要找一種文字來替代漢字,20年代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還有錢玄同主張的直接借用世界語,其本質都是想用字母文字來取代象形會意的方塊漢字。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是世界範圍內唯一一個以官方姿態支持世界語的,但矛盾的是,世界語在創立之初就有著希望超越一切國家與政府之上的初衷。事實證明,世界語在中國缺乏生活的土壤、民族的土壤與文化的土壤,不論如何支持,它也完全不可能對漢字造成實質性的威脅,所以這一階段的所謂危機也只是形式上的。
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漢字危機再一次爆發。有許多學者提出,漢字不適應計算機錄入技術的發展。彼時,「應當改革方塊漢字為字母文字」的呼聲又起。但這種觀點充其量只是一種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因為漢字即便只從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已經有了3400多年的發展歷史,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不過數十年,如果要講適應的話,也應該是計算機技術來適應漢字,而非漢字來適應計算機。果然,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漢字錄入如今已經完全不成問題。
百年以來,漢字經受著「百年孤獨」,經受了至少三次危機:一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廢滅漢字」危機,一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世界語衝擊,一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計算機技術衝擊。這三次危機分別可以定性為運動性的、政治性的與技術性的危機。對於一種語言或文字來說,其實最重要的影響要素是民族文化歷史與民族生存狀態,所以不論是運動性的、政治性的,還是技術性的危機,實際上都難以動搖漢字的根本。但眼下另一種危機的悄然萌生,對於漢字來說,卻是百年來最大的危機。
當下,漢字正在經歷百年來的第四次危機,即由漢字手筆書寫向漢字鍵盤或語音錄入的巨變所引發的母語情感的淡化,這種危機雖不引人矚目,卻是來源於最基礎的生活層面,這遠比運動層面、政治層面、技術層面的危機要更觸及根本。媒體一般將這種危機輕描淡寫地歸納為「提筆忘字」,事實上「提筆忘字」只是現象的例舉式描述,遠未觸及問題的本質。
計算機網絡所帶來的信息時代的革命,使得一切文字信息的產生、傳播與接受都完全可以依賴計算機網絡與多媒體技術而達成,人們漸漸地不再需要「提筆寫字」,於是「提筆忘字」便日漸成了一種常態。有人可能會說,這一點各國皆同,為什麼別的語言沒有不適,偏偏漢字就因此面臨危機了呢?
這是因為當前各國使用的語言文字中只有漢字是獨一無二的象形會意文字,即語素文字。字母文字大多是表音文字,可以用少量的字母符號來記錄語音,從而完成記錄語言的任務,而字母符號的存在大多規律且沒有太大變化,不論是鍵盤或語音錄入還是手筆書寫,並不會引發人們對這些字母符號的認知或情感上的錯位。但語素文字則不一樣,手筆書寫所帶來的繁複變化最易引發不同層次的感受,這也是唯有漢字才能形成書法藝術的關鍵所在。只因手筆書寫便能形成一門獨特的藝術,更不用說長期積澱所形成的深厚的母語情感。也就是說,有別於其他現存的語言文字,中國人對漢語產生的母語情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對漢字的書寫情感與書寫習慣。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母語情感是一種最難改變的情感。一個人要改變宗教信仰,是完全可能的;但一個人要改變生長環境所賜予的母語情感,則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漢語的母語情感有別於其他語言,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獨特的漢字。甚至有很多學者認為,漢字才是華夏文明最重要的載體,四大遠古文明中只有華夏文明沒有斷裂並延續至今,其根本的支撐就在於漢字,而華夏文明在發展中始終能做到多民族共存,關鍵所在,也是漢字。這樣獨一無二的漢字,這樣依賴於書寫獲得母語情感的漢字,如今漸漸遠離了筆尖與紙端,使得「提筆忘字」已成為普遍的現象,長此以往,大眾的母語情感必將淡化,國民的母語素質必將弱化,這才是百年來最大的漢字危機。
文化上的危機從來不像亡國之險那樣觸目驚心,但歷經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積累則可能引發亡種之虞。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莫不伴隨著文字的衰微與消亡,前事雖遠,亦足為鑒!所以,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場上,呼喚並激發國民的漢字書寫與母語情懷實在是一件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事情。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急需價值重塑的歷史階段,信仰的崩潰引發精神的迷亂,道德的被拋棄引發社會底線被屢屢突破,人們的眼前充斥著娛樂與物慾,如果再沒有民族文化根本的倡導與弘揚,百年而後,國民丟失的將不僅僅是母語情感,還有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實現「中國夢」的希望。
讓人欣慰的是,在「亂花已然迷人眼」的重重選秀與娛樂節目中,終於有一檔名叫《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的節目突圍而出,並受到國人的矚目。這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一個嶄新的希望,一種有力的擔當。就像它的宣傳語所說,這是「書寫的文明傳遞」,這是「民族的未雨綢繆」!雖然我們不知道它會帶來怎樣顯著的文化效果,但這種努力的方向就足以讓人怦然心動。
我們不做,誰來做?現在不做,何時做?如果你對這片熱土還有著深深的眷戀,請為漢字做些什麼,哪怕只是從書寫開始。況且,我們的母語是這樣獨特的漢語與漢字——
在我眼中,沒有一種語言,像漢語這樣優美!沒有一種文字,像漢字這樣純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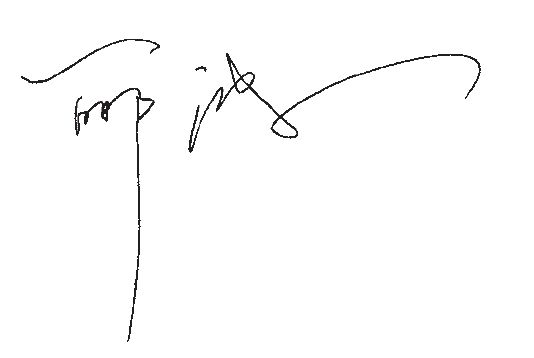
(南京師範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專業博士,漢語言文學博士後 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