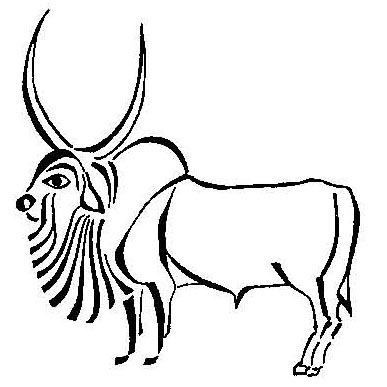
公元前1500年左右好戰的入侵者摧毀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開啟了印度歷史上的黑暗和野蠻時代。向南穿越山區的幾輪雅利安入侵者可能耗費長達300年時間才完成遷徙。在此期間,互相敵對的武士群體趕著牲畜四處漫遊,時不時停下來收穫作物,然後再次踏上旅程。這些四處遷徙的人互相爭鬥,征服他們遇到的任何土著人口。遊牧民族逐漸滲入印度的新地區,傳播雅利安語言,打破內陸森林地區各民族早期的孤立狀態,雅利安人因其尚武精神和更好的武器輕易地征服了這些森林民族。
但是,遊牧民族開始逐漸定居,過上更穩定的農業生活。畜牧業不再像遊牧和征服的英雄時代那樣享有突出的地位。更繁重的田間勞動充實了武士牧人閒暇的日常生活。但即使入侵者完全過上農業生活後,雅利安人向印度南部和東部的擴張也未停止。他們的刀耕火種耕作方式要求在舊耕地變得雜草叢生時不斷向新土地遷徙。
印度歷史上的「英雄時代」留下的遺跡很少。由於缺乏設施良好的城市或永久性的居住地,考古學者未能發掘出多少早期雅利安人的遺存。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時代留下了文獻。但這些文獻的保存應該歸功於後來的祭司對它們作了改編並應用於宗教儀式。在此過程中,原始文獻在被一代代口傳心授時經過了多次變化。結果,我們常常無法知悉哪些是真正的古代文獻,哪些是後來增添的內容。但是,最神聖和現存可能最古老的梵文詩集《梨俱吠陀》和大型史詩《摩訶婆羅多》,包含了描寫貴族弓箭手如何駕馭馬拉戰車馳騁疆場、用密集的箭矢與敵方的英雄展開殊死搏鬥的段落。這些段落證明,像希臘和中東一樣,印度也經歷了貴族戰車時代。
大約公元前900年,戰車戰術不再流行於印度。鐵器傳播到南亞次大陸,像中東地區一樣,鐵器使那些無力購買戰馬和戰車的窮人也能用盔甲保護自己。因此,鐵器時代的來臨,打破了貴族的支配地位。隨著鐵器改變戰場上的力量平衡,小城邦興起,在這些城邦內,每個戰士都有權參與政治決策。這種武裝的、原始平均主義的群體存在的證據主要來自北部,尤其是喜馬拉雅山的南麓;但是在恆河流域中央集權的大型君主國開始取代這種地方群體之前,同樣的政治結構也可能曾經更廣泛地分佈於其他地區。的確,只有當這些古老的氏族共和國臣服於一些偉大國王的武力後——這個過程在大約公元前600年達到頂峰,我們才知道它們的存在。
向恆河流域的轉移
鐵器對印度生活還產生了另一個重要後果。用這種新金屬製作的工具加速了對叢林的砍伐,特別是在恆河流域,季風帶來的大量降雨使那裡的植被非常茂盛,如果樹木被砍倒,那麼它的土壤可被開墾為非常肥沃的耕地。正如我們看到的,可能最初由東南亞耕種者培植的水稻大大提高了恆河流域的農業產量。中東農業的兩大作物小麥和大麥的畝產量大大低於水稻。因此,適宜種植水稻的地區,能養活更稠密的人口。隨著水稻的種植,人們開始長久地定居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因為通過根本改變土地的濕度,稻田的人工灌溉和排澇幾乎清除了所有的雜草。此外,為了引水到稻田而需要的圍堤、挖掘和平整工作太耗費勞力,因而遷徙到新地方定居似乎沒有什麼吸引力。於是,水稻種植盛行的結果是,全面定居的農業、永久性的村莊與城鎮中心,以及因無法逃進叢林中的空地而容易被徵稅的人口,都興起於恆河流域。
因此,到公元前800年,恆河流域取得了文明複雜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充分條件。印度河流域這次落後了許多。古老的遷徙種植方法在印度河流域仍然普遍存在。每當國王的稅吏徵稅或攤派勞役時,當地人就在森林中逃得無影無蹤,在他們之上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堅固的大規模政治體系。相反,在東部,稻田既把種植者固定下來,又給予他們一種高產量的農業,這種農業使他們能夠在交出大量糧食之餘生存下來。
因此,由職業行政人員和職業士兵維持的幾個大君主國開始在恆河流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印度河流域(很可能還包括我們一無所知的印度南部)仍然分裂為眾多的部落集團,即使統一,也只是與某個強大國王結成不穩定的宗主關係,在親信追隨者的小圈子外,這些國王缺乏真正的管理權威。但是在恆河流域,有效的中央集權君主制的發展支持了宮廷中心的興起,在宮廷裡,高級手工業技巧得以迅速地發展。地區之間的貿易也變得重要了,甚至從恆河流域的中心向四周輻射,為印度河流域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考古材料表明,到大約公元前800年,印度與美索不達米亞的海上貿易又恢復了。
從這些方面看,印度的發展與中東地區相當,只是稍微晚一點兒,文獻記錄稍微少一點兒。但是公元前800年後開始出現於印度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興都庫什山以北和以西的亞述帝國和波斯帝國盛行的大同主義世界大不相同。新興的印度文明的獨特性集中體現於種姓制度和印度宗教對禁慾和先驗的強調。這兩個特點都需要稍加解釋。
種姓
現代種姓制度是共同飲食、內部通婚並嚴禁其他人參與這兩項親密活動的集團。此外,任何種姓的成員都必須佩戴一些獨特的標記,以便他人知道誰屬於、誰不屬於這一種姓。隨著不同種姓的接觸越來越頻繁,在其他種姓面前如何舉止的明確規則也成為必需。當整個社會最終都以這些原則組織起來時,任何陌生或入侵的群體都自動地變成另一個種姓,因為其他人口的排外習性必然在就餐和通婚方面把新來者排除在外。在一些爭端中,或者僅僅通過一段時間的地理分隔,大種姓可能很容易就會分裂成小的集團。新種姓能夠圍繞新的職業而形成。在社會中找到新生計的流浪者和背井離鄉者受到周圍種姓習慣的約束,被迫一起吃住、相互通婚。
至於印度社會如何或何時根據這些原則被組織起來,仍不清楚。也許印度河流域文明本身就是建立在類似於種姓原則的某種制度的基礎之上。也可能雅利安入侵者與被他們征服的黑皮膚民族之間的互相仇視為後來印度的種姓制度打下了基礎。但是無論種姓制度的起源是什麼,後來印度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三個特點都被用於維持種姓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儀式純潔性的觀念。由於擔心會因與低級種姓接觸而受到玷污,所以「不潔的」種姓為婆羅門種姓和其他接近金字塔頂的種姓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去限制與低級種姓的人交往。
從種姓制度的另一端看,窮人和地位卑微者也有支持種姓制度的強烈理由。除了最悲慘和最邊緣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輕視某些人,這是種姓制度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心理特點。此外,比較低級的種姓常常是那些剛剛脫離原始叢林生活的集團。即使生活在不同背景、不同種姓的人一起居住的城市或混合鄉村的環境中,他們也本能地力圖維持自己的獨特習俗。其他的文明社會常常勸導或強迫新來者放棄自己獨特的習俗,並且在幾代人時間裡,把他們全部同化為文明人口。相反,在印度,這些集團通過在種姓制度內部保留他們特有的習俗而能夠一代又一代地維持其獨特的身份認同。
維持種姓原則的第三個因素是理論上的:轉世和「瓦爾那」的宗教教義。後者宣稱,所有的人生來就被劃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祈禱,剎帝利作戰,吠捨勞作,首陀羅從事不潔的工作。正式的教義把前三個種姓劃歸雅利安人,最後一個種姓為非雅利安人,並且嚴格規定各個種姓的等級,婆羅門最高,首陀羅最低。現實與這一理論相去甚遠。如果盡可能地回溯歷史,印度即使沒有數千個種姓,也有數百個,遠不僅僅是婆羅門教教義中所承認的四個種姓。但是這種理論很重要,因為當轉世思想與瓦爾那教義結合起來時,明顯的不公正和不規則就消失了。通過把種姓解釋為神創立的制度、父子世代相傳、目的是為了獎懲人們前世所造的業,轉世觀念的確為種姓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的辯護。這無疑有助於平衡現實的混亂。一個出身最低級種姓的人,如果過著完美無瑕的生活,那麼就有望在來生轉世為較高級種姓。相反,一個高級種姓的人,如果不能遵守適當的行為標準,那麼就可能轉世為較低級種姓。一個真正邪惡的人甚至可能轉世為一隻蠕蟲或甲蟲。
顯然,古代印度不存在今天看到的這種種姓制度。但是現代種姓制度是像最古老的歷史記錄那麼悠久的社會組織的派生物。例如,早期佛教故事就揭示了許多與種姓差異的有關情節,《梨俱吠陀》和其他古代文獻中的段落也暗示了類似於種姓的做法和態度。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到公元前500年,發展出現代社會種姓制度的種子就已經在印度大地上廣泛萌芽了。
種姓制度降低了政治、領土管理的重要性。對每個人來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同自己的種姓。但是一個種姓一般缺乏明確的內部管理和特定的領土範圍。某個特定種姓的成員實際上都是與其他種姓的人混雜在一起,遵守互不玷污的必要規則。任何國王或統治者都不能獲得那些自認為屬於某個種姓而不屬於某個國家的臣民的絕對忠誠。的確,普通種姓成員視統治者、官員、士兵和稅吏為找麻煩的局外人,盡可能地無視他們,只有必要的時候,才服從他們的命令。大多數印度國家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引起的。所有早期印度歷史的特點就是極其缺乏有關戰爭和政府的信息。這可能也反映了印度各民族疏遠國家和政治的基本態度。
種姓制度也使印度文明很容易把新的集團納入自己的範圍。新來者無須急劇調整從前的習俗,他們僅僅變成印度已有的眾多種姓中的一個而已。相應地,非常原始和古老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半隱藏於印度社會結構中,為了在陌生人中生存的需要而改變自己的各個民族將其延續了下來,並通過種姓這一制度,仍然保留了他們原始祖先的巫術儀式、咒語和思維習慣。
先驗的宗教
不關心戰爭和政治、容忍各種不同習俗等情況也與印度獨特的宗教變化吻合。直到最近,印度大部分宗教教義仍然是通過師生口傳心授而傳承。任何最迫切的探求真理的人也必須向幾個老師學習。因此,教義會出現各種混雜和重疊現象。此外,沒有日期幫助理清宗教思想發展的線索。保存下來的大量宗教文獻很少包括有關事件的記載,或者任何可以辨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記載。因此,任何區別思想發展脈絡的努力都必然是推理性的,而非歷史考證的。但是,推理的結果可以與歷史發展階段相吻合。當然,我們不敢簡單地肯定。
當然,現存文獻都是用雅利安入侵者的語言梵文寫成。他們還帶來了眾多的神祇,其中主要的戰爭首領和最強大的神是因陀羅,他是城市的破壞者和雷電之神。其他神祇則包含了其他自然因素和力量——天空、空氣、大地、水等等。祭司制度也伴隨入侵者而來。祭司的作用是乞求神的保佑,供奉祭品,或通過其他適當儀式以取悅神。和平時期的繁榮、戰爭得勝、長壽、健康等都是這些虔誠行為的目的。
這種宗教與印歐語系其他蠻族部落——如希臘人、拉丁人、凱爾特人、日耳曼人、伊朗人、斯拉夫人等的宗教目的和態度似乎沒有什麼顯著差異。他們都敬重自然界中或多或少被賦予了一定人性的某些方面。雖然眾神的具體情況各異,但是顯然,早期印歐語系宗教所表達的世界觀是由專門的祭司所建立的,他們至少模糊地瞭解美索不達米亞人如何把宇宙的神聖統治者看成一群吵吵鬧鬧、喜怒無常的神。蘇美爾眾神與印歐語系各民族的眾神之間普遍但不精確的相似性無法用其他的方法予以解釋。
吠陀與婆羅門
我們可以通過《吠陀》來瞭解雅利安人的宗教。用作宗教儀式手冊的《吠陀》是由一些頌歌構成,在供奉祭品的時候,《吠陀》和其他指導祭司進行宗教儀式的段落都可以被大聲朗誦。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對祭司來說,《吠陀》的語言也多少變得有些晦澀難懂。因此,通過一代一代的師徒口授,發音和音調的細節都被盡力地保持下來。世代相傳的詩文的隻言片語都事關重大,因為任何一個發音錯誤都可能使祭祀活動完全無效,招致神的不悅。
對細節正確性的優先關注,促使了從強調雅利安眾神向強調崇拜行為和祈禱儀式本身的迅速轉變。雅利安祭司也許學會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祭司所聲稱擁有的魔力。無論如何,一些婆羅門開始爭辯說,通過舉行正確的宗教儀式,他們實際上能夠強迫神賜予人們所請求的任何恩典。的確,適當的供品和祈禱儀式建立了神的世界,人們更新和穩定了自然界與超自然現實之間的關係。用這種方法,個別神的重要性和法力就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而祭司的權力和技巧則大大增強了。在被稱為「婆羅門」的經典中,這些祭司的誇張叫囂隨處可見。這些都是作為吠陀經典的註釋形式而被提出來的,據說這些註釋解釋了比較古老的文獻的真實含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註釋也篡改了古老文獻的含義。
《奧義書》、神秘主義和印度教的起源
在古代印度,祭司聲稱的擁有對神和人行使權威的要求從未得到普遍承認。雖然部落酋長和武士可能對祭司的魔法不太在意,但是他們並不迫切地把婆羅門聲稱的最高的社會地位讓給祭司。社會上更低級的人群也反對祭司的最高的社會地位。下列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不同的虔誠崇拜扎根於印度各地,並很快就變成印度最突出的宗教傳統。另一部口頭文獻《奧義書》就包含了這種宗教發展過程的證據。《奧義書》不是系統的論文,所有的細節並非都前後一致,但是它的確表達了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普遍看法。
首先,《奧義書》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認識宗教生活的目的。一個明智而聖潔的人不應該尋求富有、健康和長壽,而應該僅僅力圖擺脫無窮的輪迴。由於獲得成功,所以他的靈魂能夠融入產生靈魂的萬物,勝利地擺脫人生的痛苦、煎熬和缺憾。
其次,聖潔和擺脫輪迴的途徑不是服從祭司,而是履行宗教儀式。真正聖潔的人無須中介,因此,也無須神。相反,通過自我克制、沉思、禁慾、拋棄日常生活中的慾望,那麼成功的宗教修行者就可以達到對神的玄妙幻覺——幻想著幸福和快樂。神秘幻覺的性質和內容從來無法用語言表達。它通過個體靈魂與宇宙靈魂合而為一來揭示真理。這種體驗超越了人類的理解能力和普通語言的表達能力,是自我與萬物融合的最大福祉的預示,而這種融合是明智聖潔生活的終極目標。
《奧義書》所表達的主題和態度,與《吠陀》經典和婆羅門經典的世俗和實用語調大相逕庭,任何非神秘主義者都會問:如何解釋這種變化。也許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祭司和聖潔的人就已經知曉禁慾行為。如果事實是這樣,那麼《奧義書》給宗教生活的指導就可能表現為對起源於前雅利安梵文文學的態度和禁慾行為的默認。但是由於我們缺少前雅利安人時期宗教情況的材料,所以這種解釋仍然是推測性的。
第二種解釋認為,印度社會背景的變化是神秘主義蔓延的原因。的確,在鐵器時代興起於北印度、或多或少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少數自由人共同體開始解體,恆河流域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興起之前,《奧義書》強調的禁慾和彼岸世界就已經吸引了說雅利安語的人的注意。或許因此,被那些發現熟悉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維持的人禁慾主義所吸引,因為外來入侵者和遙遠統治者的官員已經破壞了他們父輩所瞭解的社會和政治秩序。根據這種假設,武士和統治者的後裔在追求個人聖潔的過程中,找到了已經失去的自由的替代品,而其他大多數人則享受隱退叢林的自由,遠離喧鬧的人群。當一位禁慾主義大師企圖把他的神秘經歷傳授給其他人時,《奧義書》就是在這種地方創作出來的。
第三種解釋是心理方面的。當然,懷疑論者能夠毫無困難地證明,持續的齋戒、不眠、故意克制呼吸等,也能夠產生異常的身體感受。當人們迫切地準備把這種體驗解釋為面臨某些神聖的、最終的現實時,這種體驗就取得了壓倒情感和個性的重要性。
但是對任何具有神秘幻覺體驗的人來說,這些解釋純粹是無稽之談。共同擁有這種記憶並希望更新精神變化的發起者都知道這種體驗的效力。證明是不必要的,解釋是不可能的,懷疑是不可理喻的——或者說,成千上萬神秘主義者的言行已經充分地說明了一切。
《奧義書》主張無神論的禁慾主義,所以婆羅門經典要求的煩瑣宗教儀式自然遭到反對。但是古代印度的婆羅門祭司發現了調和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的簡便方法。在他們經歷了年輕時尊敬祭司、遵守宗教儀式指令、供養家庭之後,他們認為,《奧義書》提出的方法適合人生的目的。用這種方法,《奧義書》的教義被吸收進婆羅門教,作為普通人宗教儀式的承辦者,因冒充權威而遭到《奧義書》教義直接抨擊的婆羅門教祭司竟然從容地倖存下來了。
《吠陀》經典與《奧義書》宗教傳統的融合標誌著印度教的產生,印度教也是世界大型宗教體系之一。大量宗教實踐和信仰曾經是並且仍然是印度教的一部分;為了應付祭司的儀式需要和神秘主義的理想,整個體系繼續演變。印度教繼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刺激因素是與其他更系統的宗教的接觸。
耆那教和佛教
大約公元前500年,佛教和耆那教的興起給印度教帶來了第一次外部挑戰。這兩種宗教都有歷史創立者,他們可能都生活於公元前500年左右,雖然確切的時間都不得而知。耆那教由筏馱摩那創立或再創立,佛教圍繞富有領袖魅力的喬達摩王子而興起。這兩種宗教有很多共同性。在一定意義上,它們都使《奧義書》抽像表達的觀念大眾化了。筏馱摩那和佛祖喬達摩都使個人達到涅槃,擺脫了作為宗教修行最高目標的輪迴。但是這兩種宗教的一些具體的重要教義有差別,耆那教從來沒有像佛教那樣流行。它一直是精英的信仰,要求嚴格禁慾,甚至達到餓死的程度,它的創立者就是如此。
相反,佛教是圍繞一個中等政權而創立的。喬達摩年輕時力行禁慾,但是他發現,殘酷自虐身體並不能擺脫人生的痛苦。他轉而推薦一種介於平常的自我放縱與實行嚴格禁慾之間的適中方法。他本人及其眾多信徒把時間分為沉思、宗教討論和乞討幾個部分。在雨季,喬達摩喜歡帶著一群信徒靜坐一處。在旱季,他則雲遊四方,靠施捨維生。通過消滅自我而擺脫痛苦是佛祖的終極目的。但是,這個目的——涅槃——對大多數人來說太遙遠了。與此同時,佛祖敦促他的信徒通過追求「八正道」而培養內心的聖潔,八正道就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及最重要的正定。佛祖喬達摩從未明確說明如何翻譯「正」這個詞在這些短語中的意思。他的信徒企圖倣傚他的生活,無論何時遇到什麼問題,都遵守他制定的規則。
因此,喬達摩生前就擁有一批信徒,他們對喬達摩描述的生活方式非常滿意,即使在他去世(公元前483年)後,他們仍然生活在遵守他的規則的僧團內,尊奉喬達摩王子為神聖的佛祖。英語作家一般稱這種僧團為「修道院」。事實上後來的基督教修道院與它們非常相像,因為許多佛教僧團很快便擁有了虔誠的俗人捐贈的房舍和可以帶來收入的財產,那些俗人覺得求解脫的路上需要聖潔者的幫助。
最初作為師徒共同生活的臨時團體就以這種方式最終變成了永久性團體,而且持續到我們的時代。可以肯定,佛祖的教義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微妙而急劇的變化,但是佛教僧團制度的延續仍然沒有被打破。成千上萬人的生活、情感和行為都受到這些團體及其宣揚和代表的宗教理想的影響。儘管佛教的誕生地後來抨擊佛教的虔誠形式,但是印度對周邊民族的主要影響都是通過佛教傳道僧侶而產生的,正是這些傳道高僧把佛教教義和行為方式傳播到中國、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絕大多數地區。
在印度境內,佛教在誕生後的幾個世紀裡,使《奧義書》的宗教生活方式變得普遍、溫和與定型。因此,佛教有助於給整個印度文明打上獨特的來世、神秘、禁慾傳統的烙印,為它指明發展方向,後世印度思想家和聖人從來沒有偏離這種傳統。儘管佛教早期獲得了成功,但是復興的和變形的印度教還是能夠贏得大多數印度人的支持和忠誠。這個轉變如何發生有待後文考察,值得指出的是,正是佛教自身的實踐缺陷導致這種轉變的發生。早期佛教沒有為人類生活的正常事件——如出生、死亡、婚禮、老年等等——設立什麼儀式,因此平常人的生活瑣事仍然需要婆羅門的服務,因為婆羅門保存了吠陀學術知識和祭司的複雜活動。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只為那些拒絕正常家庭生活、終生追求神聖的非凡人物提供了完整的指導。沒有傳統的儀式和祭司的幫助,其他人將無法生活。早期佛教沒有為日常生活中的危機提供解決方法。因此,印度從未變成徹底的佛教國家,印度文明也從未使自己完全適應佛教範式。
但是,公正地說,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當種姓制度和印度宗教特色變得清晰時,印度文明從整體上已經確立了它的永久特徵和特殊傾向。重大的精細化和緩慢的重大轉型當然還在後面,但是一種清晰的文化認同把當代印度與佛祖時代的印度聯繫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