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俗已經遠遠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讓它慢下來。唯一的辦法還是嘲笑惡俗。如果連這個也不做的話,那你就只能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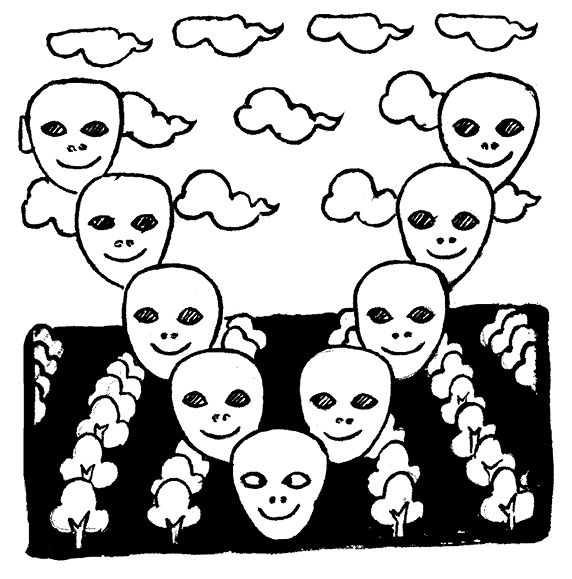
美國的愚蠢
所以說,美國是惡俗的。惡俗之所以會在美國氾濫成災,是因為在所有國家中,美國最沉迷於自我誇耀和自鳴得意,甚至超過了法國。「上帝要我們擁有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國家」,《今日美國》最近援引俄勒岡州一名護士莉莎·尼爾森的話說。正是這一普遍的信念,為美國拒不放棄對前殖民地,比如巴拿馬和菲律賓充當道德警察角色的習慣找到了借口。於是,這些國家的被告就只能被強制送到未受玷污的美國「大陸」,接受美國司法機關的審判和意料之中的恥辱。
美國是全世界道德虛偽的大本營。在近半個世紀內,美國都自視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以為對那些沒這麼幸運的國家而言,自己在所有方面都很傑出,都是他們的楷模,這一習慣使美國人很容易忽視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實。就說說目前美國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吧,我居住的這座大城市已承認的文盲就佔了人口的 40%,毫無疑問,實際比例會更高。的確,在聯合國的 158 個國家中,美國國民的文化程度只排在第 49 位。1990 年的人口普查因為一個令人吃驚的原因而遇到了麻煩:相當多的人一看到信箱裡的人口普查表,就把它給扔了,因為他們看不懂那張表,就跟他們讀不懂任何英語文章一樣,包括童話故事《三隻小熊》和《灰姑娘》。這些人就是會在火車站問旁邊的人到羅切斯特的火車停在哪個站台的人,因為他們讀不懂標識牌。還有很多人不會看時鐘,所以你會在大街上遇到攔住你問時間的人。他們並非買不起手錶,他們只是不懂得看時間。
有人會說,夠了,夠了,你說的這些都只是「少數」,不然這些人顯然就是下層平民,他們自然什麼都是糟透了的。但在美國的 6000 萬功能性文盲1大軍中,有許多人都跟喬納森·考澤爾2在《文盲的美國》(Illiterate America)一書中講到的那個職業人士一樣,謹小慎微又顯然很做作。這個人在紐約工作,他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
早上起床後淋浴、剃鬚,然後穿上深灰色的西裝下樓,在他家附近街角的小報攤上買一份《紐約時報》。將報紙整整齊齊地折好後就走進地鐵,9 點鐘到辦公室。
將折好的《紐約時報》緊挨著辦公桌上的公文包放好後,他就開始為編輯交給他的一份廣告文本設計說明圖片,那位編輯就是他的老闆。
「跟我好好講講這個稿子吧。儘管放心,我能抓到你真正想要的東西。」
那位編輯一點也不懷疑,把這看作是合理的要求。在編輯詳細闡述文本的過程中,他背下了整篇稿子,將稿子的內容迅速印在了腦海裡。
午飯時他拿著折好的《紐約時報》去了一家咖啡店,把報紙放在他的餐盤邊上,吃了一塊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後很快就回到了辦公室。
下午 5 點,他拿著公文包和《紐約時報》等電梯,下樓後再步行穿過兩個街區,去趕開往住宅區的公共汽車。他在住所附近街角的一家商店前下了車,進店裡買了一些吃的,然後就上樓了。
到家以後,他把《紐約時報》放在堆報紙的老地方。稍晚一些,他會用其中的一兩份報紙包垃圾。吃完晚飯後,他會打開電視,如果辦公室裡「有人提及某些新聞,他會依據自己從電視上得到的信息給出一個乾巴巴的、冷嘲熱諷的回答」。雖然總擔心自己會被揭穿,他還是成功地躲過了不少這樣的場合。他對考澤爾說,他常做的一個惡夢是某個時刻某個人拿出一張上面寫著字的紙,不耐煩地衝著他問:「這是什麼意思?」每次夢見這一最令他感到羞恥的景象,他都會尖叫著驚醒過來。
6000 萬文盲中肯定包括不少這樣的職業人士,永遠害怕露餡,不安地存在於這個被有教養的人掌控並主宰的世界。如果 6000 萬人都跟那個人一樣,是功能性文盲,那美國還有 6000 萬人就只具備人們仁慈地定義為「小學五年級水平」的閱讀能力。每年讀書超過一本的人只佔成年人口的 6%,而且所謂的「書」定義寬泛,包括准色情愛情小說和《如何使自己看上去比現在更棒?》一類的指南。6% 的成年人每年只讀一本「書」,那剩下 94% 的成年人對社會現實的瞭解就完全依賴電視、廣播、道聽途說、報紙(目標讀者是智力水平等同於八歲小孩的人),以及主要致力於提升讀者「自尊心」的雜誌。
所以,與同樣工業發達的國家相比,美國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著缺陷。明顯的一個缺陷,是美國在工業設計領域相對於日本的劣勢。在這個領域,如評論家道格拉斯·戴維斯(Douglas Davis)所說,「我們落後於競爭對手數十年」,這一事實卻被我們獨有的自大習慣所輕視或漠視了。「殘酷的現實是」,戴維斯指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美國的消費品都風格枯燥乏味、創意不足、做工粗糙。」同樣,任何一個睜著眼睛旅行的人都知道,在社會福利方面,美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相比顯然處於劣勢。引人注目的是,我們的謀殺率和暴力犯罪率卻遠遠高於其他的工業發達國家,再加上嬰兒死亡率是日本的兩倍,美國根本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洋洋自得。事實上,在「文明」國家中,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排在第 22 位,遠遠落後於法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比利時和英國,甚至落後於西班牙和愛爾蘭。此外,即便某人在這個國家順利地出生了,他的麻煩也並未就此終止。全美青少年死亡人數的 3/4 以上都死於自殺、謀殺或意外導致的暴力,堪稱一項世界紀錄。1990 年 3 月,《紐約時報》聲稱:「與其他 11 個工業發達國家相比,美國孩子更有可能生活貧困、生活在單親家庭,並在 25 歲之前被殺害。」其中許多青少年是被燒死的,在所有工業發達國家中,美國的防火安全紀錄最差,更不用說引人注目的吸毒人數了。
將美國對暴力的嗜好、對武器像得了相思病一般的熱愛,和對毒品的渴望放在一起,你就會有這樣的發現(《紐約時報》,1990 年 6 月 27 日):
到目前為止,美國已成為工業發達國家中的殺人首都
據聯邦調查局報告,美國年輕人中的「殺人率」(即謀殺率,見「惡俗語言」)是其他工業發達國家的 4~73 倍。他們透露國內 3/4 的謀殺案都會使用武器,而海外只有 1/4 的謀殺案會使用武器。
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幾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槍支;在這個勇者的故鄉,沒有人會被認為是真正勇敢的,因為可能一場架還沒吵完,就有一把槍已被製造了出來。
此外,美國人的愚蠢和無知長久以來都是歐洲人的笑柄。不是「美國的青春活力」,我們現在談論的是「美國的愚蠢」,按克裡斯托弗·拉什3的定義,也叫「麻木的擴散」。學校竟然連受半瓶醋教育的公民都培養不出來,這已經不是新聞了。美國高中 17 歲的學生中只有 42% 的人能讀懂一篇報紙社論,還是最愚蠢的報紙上的社論。這些學生如果不是「理解力」有問題,就是沒能聰明地掩飾住自己完全沒有閱讀能力的事實。學生學習能力測試分數日益下滑的醜聞已經傳了很多年,從 1969 年到 1989 年,志在考取「學院」的高中畢業生的分數就下跌了 53 分。在大多數美國大學裡,大多數學生要將第一年(有時第二年也要算上)的時間花在「學習」上,這種「學習」只能稱之為補習。最近,紐約電話公司不得不從 5.7 萬人中篩選出 2100 名足夠聰明的人,去擔任安裝修理工。現在,如果你聽到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抱怨他面試的人,即使畢業於最好的法學院,也不能作清楚的口頭表達和書面表達,更不用說生動流利地表達了,那你也不必感到吃驚。這些人就是當今的電視和視覺環境培養出來的無能的年輕人,不理解法律,也不能精確地理解或有效地使用語言。
許多教師來自智力低下的階層,一所公立學校的老師可以作證:「我所在學校的一名二年級老師有一天走到我跟前,問我一年有幾個星期……接著又問一年有多少天。」當她被問到是怎麼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這位有學問的老師回答說她是在小學裡學會的。顯然,學校的全部課程對許多老師來說太難了,他們只好繞開那一大堆他們不懂的東西,其實那些課程為了避免所有學生都學不懂,已經設計得很簡單了。說到高校的狀況,雖然E.D.赫希4認為要具備「文化素養」,人們就有必要瞭解標準的東西,這種觀點可能有些過分,但每天仍然有證明公眾無知的令人震驚的新例子出現。某家全國性報紙最近刊登了一幅布什總統接受一個榮譽學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從他頭上往下披的那一刻拍的,圖注寫道:「布什總統出席他的文學博士學位授予典禮,正被披上飾帶。」這家報紙連學位服的披肩都說成了「飾帶」,卻居然獲得過幾次普利策獎。
美國這種與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見到。所有簽銀行支票簽了 50 年的人都會注意到,甚至在這麼重要的物品上也存在愚蠢。如今,有人覺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個小方框,這樣金額的數字就可以填在裡面了,好像不這麼做的話,人們就搞不清楚該把數字填在哪裡。支票背面也有一項重大的創新,有一個確定的地方讓你簽名,好像人們都不知道該在支票的哪一頭簽名似的。看來有必要通知一下準備寄信的美國人:「郵資不足的話,郵局將不予投遞信件。」這在過去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還有能「正確拼寫」的打字機。這東西之所以這麼流行,是因為沒有幾個「書寫者」能很好地駕馭自己的母語,好到不需要機器幫忙就能拼寫正確;還是在這個老百姓愚蠢至此的國家,人們花了大筆的錢買東西,卻絲毫看不出所謂的「折扣退款」有多荒唐可笑,他們從不指望商品的價格在出廠時就能降一些。想想吧,你鄭重其事地把錢遞過去,然後等著其中的一些被裝腔作勢地遞回來,然後感覺自己在這場討價還價的交易中賺了一把;還有一種新式的做法:全國鐵路客運公司的乘客在被允許進入站台前,要接受仔細的檢票。鐵路客運公司的動機很明顯,因為文盲(平均每天有 30% 的乘客可能是文盲)既讀不懂車票也讀不懂大門口指示目的地的標識牌;還有會出現如下現象的這種文化:不僅當地的天氣預報,全國各地的天氣預報也都被電視台看作電視新聞中一個有趣的話題,(上帝原諒我這麼說)所以值得花大價錢請一個名人來正經八百地對天氣評頭論足。
這個國家將數億美元花在「探索」外層空間上,同時卻有數以百萬計的窮人和飢餓的人像印度加爾各答人一樣露宿街頭;成百上千萬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如此空虛,以致他們給自己作定位並獲取自尊的主要方式就是去「購物」;這個國家還垂涎於將東歐美國化,在那裡培植給我們帶來白色加長型豪華轎車、唐納德·特朗普、吉姆·巴克和塔米·巴剋夫婦、利昂娜·海姆斯利,以及米爾肯5和伯爾斯基6一類人的價值觀。
這個國家將一個過氣的電影明星選為總統,以此證明自己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的價值觀。這個電影明星對現代和當代歷史都很無知,以致長期在有知識的人中間上演著一場鬧劇。他對世界的現實是如此地漫不經心,在 1980 年代後期竟然斷言已經沒有幾個活著的德國人還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了,這樣的總統卻還得以連任。他信奉的主要觀點是:校園禱告與廢除富人的稅賦都是國家需要的,而窮人和無家可歸者都是自找的。
美國的愚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肯定不是從富蘭克林和傑斐遜開始的。一些粗魯的無神論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傢伙(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企圖將「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風」(一位社論作者的說法)的起源定在 19 世紀 30 年代。其時,天使摩羅乃告訴約瑟夫·史密斯7,有一些埋在地下、記載著大量悲慘事跡和訓喻的金頁片8要給他看,看完後,約瑟夫·史密斯就說服一大幫鄉巴佬創建了一種新的宗教。馬克·吐溫認為美國的愚蠢在他的時代就已經很發達了。也有些人說隨著瓊斯城的集體自殺9,這種愚蠢在 1978 年到達了頂點。到今天,這場愚蠢運動已經非常明瞭了,足以令人聯想到當代兩個隨之產生的現象(如果這兩個現象不是原因的話)。
第一個現象是電視搞笑頻道提示觀眾何時該笑(如果擠眉弄眼和誇大其詞都不奏效的話),電視台還需要使廣告針對那些最無知、最容易輕信、心理上最沒有安全感的人。懷疑和評論類節目已被電視台嚴厲地刪掉了,要是這類節目出現在電視上,電視節目就再也無法成為一種令人滿意的愚蠢工具了。
第二個現象是公立中學的垮台,玩忽職守的學校管理者最後一次被見到是什麼時候?
這兩個現象是導致我們的智力和文化出現困境的主要原因,對此大家似乎已經取得了廣泛的共識。芭芭拉·艾倫萊徹簡明扼要地總結了「幾十位電視評論員」的發現,然後指出「由於電視與『艾波卡特中心』式教育10結合在了一起,美國的文化已經私有化、粉碎化,並也許不可逆轉地白癡化了。」即便一些人對智力和文化出現困境的確切原因持有不同的見解,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愚蠢的一個小代價,是美國的經濟實力轉移到了日本;而一個大代價,是徹底摧毀了美國的舒適、差異化、複雜和魅力,這是一個國家適於定居的要素。
使這種愚蠢加劇的,是近年來技術的迅速複雜化。當今的美國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巨大的堆積物,在裡頭,並不特別敏銳、專注的人們被迫操作一種特別複雜的技術,而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總是勝過別的國家。難怪美國四處都潛伏著謬誤和尷尬,難怪掩飾和自誇(也就是惡俗)變成了最受喜愛的國家風格。今天的一個標準景觀,是一位焦慮的年輕人要求別人給他 5 分鐘時間完成一筆簡單的零售交易。他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是為了滿足那台怪物一樣嗡嗡作響、時而呼嘯時而哼唱的機器的要求,這台機器既是點鈔機、當前庫存賬目、發票開票機,又能防止僱員偷盜,令僱員自重。每一名僱員都是一台機器的跟班,那個茫然困惑、微不足道的年輕職員,不過是面對不斷增加的刻度盤和指示燈的飛行員的一個簡單版本。那些增加的刻度盤和指示燈往往根本就用不上,飛行員只好偷偷切斷它們的電源,以免工作變得太複雜,自己無法勝任。
這一切自然會造成過度彌補,這常常又導致了某種形式的惡俗。大多數人經歷的真實的美國生活是如此地枯燥乏味、單調、胸無大志,遠離了過去的傳統,又難以跟歐洲文化產生共鳴,所以需要被「提升」,並被加工成某種美好的東西。惡俗於是成為全民空虛和遲鈍的一種可以理解的表現,並且,其形式至少能代表美國人對卓越和價值的幻想。舉個例子,如果一個城鎮沒有一家值得光顧的餐館,那麼,與現有的餐館老闆合作玩一場惡俗的遊戲,對當地人而言也算一種安慰吧?這個遊戲其實就是笨拙地模仿正宗的餐館:正兒八經地對待華而不實、狗屁不通的菜單,冒牌的法國菜,以及像芭蕾舞表演一樣的酒水服務。因為要表現惡俗,就得有兩個演員,一個充當表演者,另一個充當觀眾,兩個人必須共同致力於顛覆真實的陰謀;如果一個城鎮沒有美,沒有個性,沒有魅力,居民都是財迷、市儈和自滿的鄉巴佬,那他們跟當地裝腔作勢的「藝術畫廊」兼禮品店合作,得到一些醜陋的、批量生產的雕塑仿製品,弄得好像它們是真的「藝術品」,這也算一種安慰吧。
恐怕沒有必要在這裡指出,並非美國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惡俗的。一些品味存活了下來,足以將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趕出視線之外,不讓他在公眾面前說話11;這些品味也足以讓一些人認識到(儘管含蓄而無聲)越南戰爭是一件丟臉的事。美國的有些東西的確不錯,甚至非常好,比如《麥卡-沃爾特法案》12一類愚蠢行為出現之前開放的邊境;此外,只要美國公民是自由的這一說法仍然成立,他們仍然可以被邀請去周遊世界;再加上《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話,你就擁有一大堆讓人羨慕的價值觀了,幾乎值得你為它們去死。外交官兼學者喬治·F·凱南13瞭解這一點,儘管他在新作《生活速描》(Sketches from a Life)中給了美國一個糟糕的評價。他在書中承認,像「蕭瑟暗淡」這樣的詞能最好地描述他今天看到的祖國。他解釋道:「讀者可能會以為我只看到了醜陋、庸俗和墮落」,但他總結道,是單純的喜愛之情使他的目光停留在這些污跡上,「我如果對這個地方沒有屬於自己的一種熱愛,那它表面上的這些瑕疵就不會如此有力地擊中我……」
一年中總有那麼一天,美國接受到的只有讚美,那一天就是 7 月 4 日。在其他時候,希望美國變好的人們就要全力以赴地將美好與糟糕,尤其是與惡俗區分開來。
惡俗的未來
惡俗的未來浩瀚無邊,類似 1879 年馬修·阿諾德1所說的詩歌的未來。他當然是錯的,但如果我們以為只要痛扁一頓惡俗的人或列出他們的名字,就可以妨礙惡俗的進程,那我們就錯得更離譜了。新一任呆滯女神已經坐到馬鞍上了,她的僕人「貪婪」、「無知」和「炫耀」也已隨侍左右。簡單地說,惡俗已經遠遠地走在了前面,任何力量都休想一下子讓它慢下來。
即便我們炸毀師範學院;將航空業國有化;將大學要求的平均成績恢復為C(一般),而不是現在的B(良好);在高中重新開設拉丁語課程;不再出於貶低的目的,稱兒童為「小傢伙」、稱警察為「條子」;取消校際體育比賽;抑制國民自吹自擂的衝動;提高資本利得稅;教會一代人嘲笑廣告,並對占星術嗤之以鼻;建造不會坍塌的橋樑;遠離外層空間;讓有教養的人知道,評論是他們的主要職責;有品味地熟練地說、寫英語及其他語言;召集無家可歸的人組建一支新的國民衛隊;拍攝有智慧的電影;在海軍中制定更高的勇氣標準和紀律標準;創辦幾家成熟老練的全國性報紙;當餐館經理過來問晚飯吃得好不好時,讓惡俗餐館的食客有勇氣說「不好」;丟棄沾沾自喜的「冷戰」精神病殘留的一切心態;改善公共標識的措辭、提高公共雕塑的品味;讓有藝術才華的人設計郵票和硬幣;將公共電視台變成與任何商業都沒有瓜葛的媒體。
但這一切都不大可能實現,所以唯一的辦法還是嘲笑惡俗。如果連這個也不做的話,那你就只能哭了。
1 functionally illiterate,聯合國於 1965 年在德黑蘭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會基本的讀、寫、算,卻不能識別現代信息符號及圖表,無法利用現代化生活設施的人。——編者注
2 Jonathan Kozol(1936—),美國作家、教育家、行動主義者,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編者注
3 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編者注
4 E﹒D﹒Hirsch(1928—),美國教育家、解釋學家。——編者注
5 Michael Milken(1946—),20 世紀 80 年代馳騁華爾街的「垃圾債券大王」,J﹒P﹒摩根之後美國金融界最有影響力的風雲人物,後因 6 項重罪指控被判 10 年監禁,賠償和罰款 11 億美元,並被永遠逐出華爾街,不得再從事證券業。——編者注
6 Ivan Boesky(1937—),因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一起華爾街內部交易醜聞而出名的美國股票交易員。——編者注
7 Joseph Smith Jr.(1805—1844),摩門教創始人。——編者注
8 上面的內容經約瑟夫·史密斯翻譯後,就成為摩門教的教會正典《摩門經》。——編者注
9 1978 年 11 月 18 日,美國 912 名基督教人民聖殿派教徒追隨教主吉姆·瓊斯死在偏遠南美叢林英屬圭亞那所謂的「瓊斯城「。其中一些成員是被槍殺的,一些被強迫喝了毒藥,大多數人服毒自殺。——編者注
10 艾波卡特中心也稱為高科技館,教育性比較強,有較多科教的部分。——編者注
11 美國拳擊手穆罕默德·阿里詼諧幽默,喜歡用語言和詩來愚弄對手。——編者注
12 McCarran-Walter Act,即 1952 年修訂的《移民與國籍法》,該法規要求不僅對移民,對訪美人士也要進行嚴格的意識形態檢查。——編者注
13 George F. Kennan(1904—2005),美國外交家、歷史學家、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冷戰」時代的頂級戰略家。——編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