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7年,弗雷維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一世(1)成為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
這位來自烏斯庫布(在後來的戰爭中爭議極大的一個鐵路連接點)的塞爾維亞農夫不喜歡「書本知識」。他一聲令下,古雅典的哲學學派便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基督教僧侶入侵尼羅河谷數百年後,僅存的一座埃及神廟也被他下令關閉了。該神廟坐落在一個名為菲萊的小島上,靠近尼羅河的第一個大瀑布。
在人們的記憶中,這裡一直是崇拜愛西斯(2)的聖地。由於某些原因,非洲的、希臘的和羅馬的神都沒能在這兒站穩腳跟,而愛西斯女神卻始終受到人們的崇敬。到了公元6世紀,只有在這裡才能找到懂得像形文字書寫藝術的人。少數宗教僧侶依然在此從事著這種古老而神聖的藝術,埃及其他地方的人們則早已將其遺忘。
這時,隨著農夫出身的那個文盲皇帝查士丁尼的一道旨意,該神廟和附近的學校都成了國家財產,神廟中的雕像和繪畫等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館,僧侶和書寫匠們則被投進監獄。當他們中的最後一個人在饑饉中悄然死去時,那古老的象形文字書寫藝術也就自此消失了。
這簡直是巨大的遺憾。
倘若查士丁尼(這個上帝該降罪於其身的傢伙!)行為不如此決絕,哪怕是只留下幾位懂得古象形文字的書寫匠,那麼,今天歷史學家的任務就要輕鬆很多。所幸由於商博良(3)的天才,我們現在得以重新讀寫出那些原本匪夷所思的文字,但是要想理解留傳後世的文字究竟有什麼深意,對我們而言,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對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來說,也都有過這樣的遺憾。
蓄著奇怪的大鬍子的古巴比倫人,當他們虔誠地感歎「有誰能夠理解天神的忠告」時,腦子裡究竟想的是什麼呢?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一批批刻滿經文的泥版(4)。他們日復一日地祈禱,盡心盡力地詮釋神靈的律條,且把神靈的旨意鐫刻在聖城的石柱上。然而,在心靈深處,他們對神靈又懷有怎樣的情感呢?他們時而是最寬容的人,鼓勵僧侶們研究天國,探索陸地和海洋;時而又是最殘暴的劊子手,用駭人聽聞的酷刑懲罰那些疏忽敬神禮儀的人。
緣何如此?直到現在,這仍然是個未解之謎。
我們派出了探尋隊到尼尼微(5),在西奈的沙漠中發掘搜尋,破譯的寫滿楔形文字的書簡腓起來足足有幾十米之長……我們在埃及,在美索不達米亞(6),苦苦尋覓著開啟這神秘而智慧的寶庫前門的鑰匙。
就在這時,我們幾乎是完全偶然地發現,這座寶庫的後門始終敞開著,人們可以隨意地進出。但是,那道不大的方便之門不在阿卡德(7),也不在孟菲斯(8)周邊。而是隱匿於叢林深處,且幾乎被異教廟堂的木柱遮擋。
我們的先輩在尋覓易於劫掠的對象時,曾經接觸過他們欣欣然稱之為「野蠻人」或「原始人」的人。然而,他們之間的會面並不令人愉快。
那些可憐的異教徒誤解了白人的意圖,用長矛和弓箭相迎。來訪者則以大口徑彈槍回敬。
之後,這不同世界的人們就難得有機會進行心平氣和、不帶偏見的交流溝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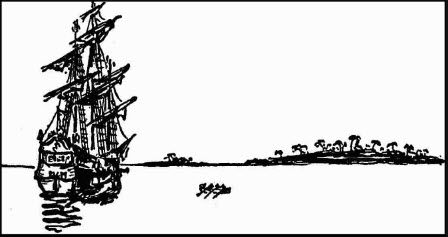
東西方的相遇
原始人總是被描寫成一無是處的遊民,他們骯髒、懶惰、游手好閒,崇拜鱷魚和枯樹,理應得到不幸的報應。
到18世紀,情形有所改變。先是讓·雅克·盧梭開始透過傷感的淚水,觀察眼前的世界。他的同時代的人被他的觀念深深打動,便紛紛掏出手帕,一起落淚了。
愚昧的原始人成了他們最熱衷的話題之一。在他們的筆下(儘管他們從未曾見過一個原始人),原始人是環境的不幸犧牲品,但這些人真正具備人類的一切美德。只是如今這些美德已經被3000年的腐朽文明體制銷蝕不見了。
時下,我們對這個領域有了更多的瞭解。
我們研究原始人,猶如研究比他們稍微低級一些的高等家畜。一般說來,兩者的關係並不十分疏遠。
付出辛勞總會有所回報。我們漸漸懂得了,原始人其實就是生活在更惡劣環境下的我們自己。只是他們還沒有被神感化罷了。通過對他們的仔細研究,我們開始瞭解尼羅河谷和美索不達米亞半島的早期社會。通過對他們的徹底認知,我們才得以窺見人類所具有的很多奇特的天性。只是這種天性已被過去5000年中形成的行為與習俗深深地掩蓋起來了。
這些發現不一定總能讓我們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對我們早已脫離的環境有所瞭解,加之對已經取得的業績的欣賞,就會讓我們更有勇氣完成自身的工作。如果還有別的什麼,那就是對那些落伍的遠親兄弟,我們會抱一種更寬容的態度。
這本書並非一部人類學手冊,它是一部表現「寬容」這一主題的作品。可是,寬容是一個非常廣闊的主題。我們很容易跑題,一旦偏離正題,天曉得我們會落腳到何處。
因此,最好還是讓我用一點兒篇幅,準確而具體地闡明我所講的「寬容」究竟是什麼。
語言是人類最具迷惑性的一項發明,所有的定義都難免專斷任意。所以,那些謙恭的好學之士最終要接受大家公認的權威。
我參考的是《不列顛大百科全書》。該書第26卷第1052頁上寫道:「寬容(源自拉丁語tolerare「容忍」一詞),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異於自己或傳統見解的觀點有耐心與公正的容忍。」或許還有其他的定義,不過就本書的目的而言,不妨就遵從《不列顛大百科全書》的釋義。
既然我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宗旨,就再回到原始人那裡吧!我要向你們敘述的是從有記載的最早期的社會形態中關於寬客我發現了什麼故事。
通常人們總是認為原始社會十分簡單,原始人說的只是一些嘰裡咕嚕的簡單語言,原始人都無憂愁地自由自在,只是當世界變得「複雜」之後,這種自由無憂的狀態才消失了。
然而,最近50年來,探險家、傳教士和醫生們在中非、北極地區及玻利尼西亞附近的土著人中進行的調查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原始社會極其複雜,原始語言的形式、時態和變格比俄語、阿拉伯語還要多。原始人不僅是現在的奴隸,還是過去和將來的奴隸。
一言以蔽之,原始人乃生於憂患死於恐懼的不幸生靈(他們並非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自由無憂)。
我們已經習慣認定那些勇敢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興高采烈地遊蕩,到處尋覓野牛和戰利品的情形,不過,目前的結論跟這樣的畫面相去甚遠,卻更接近實情。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我曾閱讀過很多關於奇跡的故事,然而,它們始終未涉及這樣一樁奇跡——人類緣何能夠生存下來的奇跡。在哺乳類動物中,人類幾乎可以說是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強的一種,為什麼卻可以抵禦嚴寒酷暑,抗拒疾病與猛獸,最終又是怎樣成為萬物之主宰的呢?這個問題我不打算在本章中就加以解答。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人類絕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完成這些事情的。為了獲取成功,人類必須把自己的個性融入部族的共性中去。所以,原始社會只有一個支配所有的觀念:求生慾望。然而,生存是非常艱難的。任何想法都必須服從一個高於一切的要求:生存。
個人是微不足道的,集體高於一切。部落是一座可以移動的堡壘。部落中人依靠群力得以自食其力。部落是獨立且排外的,唯有如此,部落中人才能獲得安全感。然而,問題要比初看時複雜得多。我剛才所陳述的,只對可見的世界有效,但在人類發展的早期,與不可見的世界相比,可見的世界簡直不值一提。
為了徹底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謹記:原始人和我們是不一樣的。他們並不熟悉因果法則。倘若我不小心接觸了有毒的常春籐,我就會責怪自己粗心大意,急忙去找醫生。期間,我還會叫人把那東西盡快剷除掉。分辨因果關係的能力告訴我,毒籐會誘發皮疹,醫生會給我一些止癢的藥物,只要除掉那些毒籐,這種痛苦的經歷就不會再次發生了。
真正的原始人的反應會完全迥異。他根本不會把皮疹和毒籐聯繫在一起。在他生活的世界裡,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的。他的那些死去的首領變成了神靈,死去的其他人變成了魂魄,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見的成員,無時無刻不陪伴著部族中的每一個活著的人。他們與活著的每一個人同吃同睡,並為其守護門戶。
他的本職是讓這些神靈和魂魄待在身邊或贏得他們的友誼。倘若他做不到這一點,就會立刻遭到懲罰。由於他不清楚如何隨時隨地地討好所有的神靈和魂魄,所以,他總是處於膽戰心驚的情緒中,擔憂因神靈和鬼魂的報復而遭遇不幸。
因此,他碰到一小點兒不同於往常的事情,也會將其看成某位看不見的神靈或魂魄在作怪,並不追尋這些事情的真正源頭。當他看到手臂上起皮疹的時候,不會說「該死的毒籐」。他們會自言自語地嘀咕:「我肯定是惹怒了哪位神靈了。這是他在懲罰我。」之後,他會跑到巫醫那裡,不過不是向巫醫討要一些能消解毒籐的藥物,而是去乞求一張「符」。這張「符」一定要能鎮住那位發怒的神靈施加給他的「符咒」才行。
而對於那誘發皮疹並且給他帶來痛苦的毒籐,他卻任憑它繼續生長在原處。要是剛巧來了個白人,這個白人用一桶煤油把毒籐燒燬了,他還會咒罵這個白人多事。
於是,這樣一個把每件事都視為某個不可見的神靈直接干預的社會,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嚴格遵從貌似能夠消除神怒的律條或法則。
根據原始人的觀點,這樣的律條或法則是存在的。他的先人將其制定下來,並傳授給了他,他就必須保有它們,且將其絲毫不動地傳給他的子孫,這是他最神聖的職責。
這種現象在我們看來,的確荒謬不經。我們信奉的是成長、發展以及永不停息的改進。但是,「改進」只是近代才逐漸形成的概念。在所有低級的社會形態中存在一個典型的共同之處:即生活其中的人們覺得自己擁有的就是世上最完美的生活,他們從來不曾想有哪些應該改進,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還有另外的天地。
既然這一切都被理所當然地看成真理,那麼,怎樣才能防止有人改變律條或法則及改變社會的既成形態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如果有人拒絕遵守代表神的意志的律條或公共法則,就立即給予懲罰——說得更直截了當一點,即依靠僵化的專制體制。
也許這樣表述會讓人覺得原始人是最專制的人類(他們最不寬容)。事實上,我的本意並非是侮辱之。所以,我要趕緊補充說明一句:在原始人的生存環境下,專制是必須的。如果容許有任何成員對部落的律條或法則指手畫腳,就會威脅到整個部族的人身安全和人心的安定,部落的生存就會由此陷入危險之中,這可是非常大的罪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數量相對有限的一小撮人,他們是如何維護這套口口相傳的複雜的律條體系的呢?要知道,今天我們雖有成千上萬的軍隊和警察,倘若要執行幾部並不複雜的法律,依舊是件困難的事情。
說起來也很簡單。
原始人比我們聰明得多。他們仗著精明的估算,做到了使用武力做不到的事情。
他們發明了「塔布」(9)這一概念。也許「發明」這個詞用得有點不夠恰當,這樣的東西不大可能源於突然而至的靈感,而只能是在長年生活經驗中慢慢摸索而出的結果。不管怎麼說,非洲和玻利尼西亞的原始人想出了「塔布」,由此而使他們自己免除了很多麻煩。
「塔布」這個詞來源於澳大利亞。我們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義。我們自己的生活中也充滿著「塔布」(即禁忌)。簡單地說,就是那些我們不能說的話,不能做的事。比如在餐桌前不能說我們剛剛做的手術,不能把湯匙放在咖啡杯裡,等等。只是我們的禁忌本質上沒有那麼嚴重的內容罷了,它們通常只是日常禮儀上的一些規定,對我們的個人幸福影響不大。

塔布(禁忌)
可是對於原始人而言,塔布(禁忌)可就至關重要了。它們意味著超越於這個世界的某些人或無生命體。如果使用希伯來的同義詞,即「神聖的」,不可以隨意談論或觸及,否則就會有當場送命或長期遭受痛苦的風險。總而言之,禁忌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宗教體系,會毫不憐憫地懲罰那些膽敢違抗祖先魂靈意願的人。
到底是教士發明了塔布,還是為了維護塔布才創立了教士這個職業,這個問題仍有待解決。既然傳統要比宗教古老得多,那麼更可能是塔布早在巫師和巫醫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後者初一現身,就成了塔布觀念最堅定的捍衛者,且由於他們運用塔布的本領如此高超,使得塔布成了史前時代「嚴禁……」的象徵。
當我們初次聽到巴比倫和埃及的名字時,塔布在這些國家還處於盛行的發展階段。塔布雖說並不像後來在新西蘭所發現的粗糙、原始的那種形式,但已經演變為一種約束人們行為的規範,這種情形如同我們所熟悉的基督教十誡中,那六條「汝不能……」式的戒律。
毋庸置疑,在那些國家的早期階段,「寬容」的概念是完全不為人所知的。
我們有時候誤認為是寬容的表現,其實不過是由於無知而造成的漠視。
在那些國王或教士的身上,我們完全看不到一點(哪怕是含糊不清的)跡象,允許別人行使「行動和判斷的自由」,或者「對異於自己或傳統見解的觀點有耐心與公正的容忍」,這可已經成為我們當前時代的理念了。
因此,本書對通常稱為「古代史」的史前歷史並無興趣。即使有,也是以一種非常否定的方式。
爭取寬容的鬥爭是以個體的覺醒為前奏的。
這一最偉大的現代啟示,其榮譽應該歸功於希臘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