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而且很有根據)這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沒有軍銜的軍官們的戰爭。將軍、上校和三星戰略家坐在某個鮮有人光臨的大別墅的大廳裡,守著孤獨的燈光,望著數米長的地圖沉思,直到想出一點新戰術,使他們能得到約1.3平方千米的領土(以大約3萬人的喪生為代價),而與此同時,下級軍官、中尉們卻在一些有聰明頭腦的下士的鼓動和幫助下,從事著所謂的「黑活」,最後導致了德國防線的崩潰。
為精神世界的獨立進行的偉大戰鬥與此類似。
沒有投入數十萬兵力的前線交戰。
沒有為對方的炮兵提供順手靶子的絕望衝鋒。
我說得更進一步,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會不時驅使人們打聽那天早上燒死了誰,第二天下午誰又會被絞死。然後他們或許會發現,有幾個置生死不顧的亡命徒還在繼續為幾項自由原則(這幾項自由原則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內心不贊成的)而戰鬥。但是我認為,這樣的消息只會使人們輕歎惋惜罷了。不過,要是自己的叔父遭遇如此可怕的下場,親戚們一定會悲痛欲絕。
情況大概只會如此。殉道者為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的功績不能簡化成數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或者馬力的概念表示。
攻讀博士學位的勤奮學生,會認真閱讀《喬達諾·布魯諾文集》,通過耐心地搜集所有充滿感情的話語,諸如「國家無權告訴人們應該想什麼」「社會不應該用劍懲處那些不贊同公認的教理的人」,寫出以《喬達諾·布魯諾和宗教自由的原則》為題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論文。
但是,不再研究那些致命課題的人,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應該有所不同。
我們在最後的分析中說過,有一批虔誠的人士,他們不僅對當時的宗教狂熱非常震驚,也對人們頭上的枷鎖很是震驚,各國百姓不得不在枷鎖下生活。於是他們揭竿而起。這些人都是貧寒之人,除了背上的披風以外,別無長物,甚至常常連睡覺的地方都得不到保證。不過呢,他們胸中燃燒著聖火,他們到處奔走,演講、寫作,把學術精湛的學府裡的博學教授拖進高深的爭論之中。在普通的鄉間酒館裡與樸實的鄉巴佬進行辯論,並且一如既往地向他人宣講要善意、理解和仁愛地待人。他們帶著書籍和小冊子,穿著破爛的衣服,四處穿梭,最後,或者患肺炎在波美拉尼亞的某個處於窮鄉僻壤的小村裡悲慘地死去,或者被蘇格蘭村舍裡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處死,或者在法國外省的大道上被車輪碾死。
如果我提到喬達諾·布魯諾(1549—1600年)的名字,我並不是說他是這類人中唯一的一個。不過他的生活、他的理念、他為自己認為正確合意的東西所產生的永不停息的熱情,在所有先驅者中的確是典型,足可以被奉為楷模。
布魯諾的父母都是窮苦人。小時候,布魯諾是個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沒有什麼特殊的天分,只是按照一般慣例,讀完通常的課程便來到一家修道院。後來也成為一名多明我會(1)的教徒。不過,他與這夥人格格不入。因為多明我會教徒熱情支持所有的迫害,當時被稱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們都很機警。異教徒根本不需要把觀點寫出來以讓追蹤的密探嗅出氣息。一個簡單的眼神,一個手勢,一次聳肩膀,就常常足以洩露一個人的異教徒身份,由此他也就被帶進宗教法庭。
布魯諾成長在對一切都要俯首聽命的順從環境中,他是怎樣成為叛逆、丟棄《聖經》而捧起塞諾和阿納克薩哥拉的著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這個奇怪的新手還沒有完成規定的課程,就被多明我會驅逐了出去,成為大地上的一名流浪者。
他穿越過阿爾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險穿過了這個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羅納河和阿爾弗河交匯處建起的強大堡壘裡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布魯諾去日內瓦的路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離開了,他們發現這裡和那裡總有那麼一個內在的精靈迷惑著人們的內心,改變一個教義並不一定意味著變更了人們的心靈與頭腦。
布魯諾在日內瓦住了不足3個月。城裡擠滿了來自意大利的難民,他們給這個同鄉弄了一套新衣服,還為他找了個做校對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就讀書寫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圖書,終於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紀教科書所宣揚的暴政不粉碎,世界便不能進步。布魯諾並沒有像自己的著名法國老師走得那樣遠。他不相信希臘人教誨的一切都是謬誤。但是,16世紀的人為什麼還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4個世紀就寫下的詞句的束縛呢?是啊,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從來都是這樣。」正統信仰的支持者這樣回答他。
「我們與祖輩有什麼關係,他們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讓死去的人死去吧!」這個反傳統觀念的年輕人說道。
很快,他就被警方找上門來,建議他最好打點行李到別的地方碰運氣去。
布魯諾以後的生活便是不停地到處奔波,想尋找一處有一定程度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卻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他從日內瓦來到里昂,又到圖盧茲。那時他已經開始研究天文學,並成為哥白尼學說的熱情支持者,這是危險的一步。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都在異口同聲地高喊:「地球圍繞大陽轉動?地球是圍繞太陽轉動的普通行星?呸!呸!誰聽說過這種胡言?」
圖盧茲也使布魯諾感到不快了。他橫穿法國,一路步行抵達巴黎,接著作為法國大使的私人秘書來到英國。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國的神學家並不比大陸的神學家強到哪裡去。也許他們只是稍微實用一點兒罷了,比如說,在牛津大學,他們並不懲治犯有違反亞里士多德教誨錯誤的學生,而是罰他10個先令。
布魯諾變得喜好諷刺、挖苦了。他開始寫一些洋溢著文采卻又非常危險的散文和對話(以宗教、哲學、政治為主要內容)。在對話中,整個現存的秩序被弄得亂糟糟,不得不接受細緻但絕無奉承之意的檢查。
他還講授過他最熱衷的科目——天文學。
然而,對受到學生歡迎的教授們,學院的當權者是很少笑臉相迎的。布魯諾又一次被婉言勸離。他回到法國,又到馬爾堡。不久前,路德和茲溫格爾曾在那裡爭辯過在虔誠的匈牙利伊麗莎白城堡中發生的化體(2)的真正本質。
天哪!他的人還沒有出面,他那「自由派」的大名就先於他傳到了。他連授課都沒得到允許。威登堡應該好客一些。可是,這座路德派信仰的堡壘已經慢慢被加爾文博士的教徒攻取。從此以後,像布魯諾這樣有自由傾向的人們就失去了容身之所。
他又向南行,到約翰·赫斯的地盤碰運氣。等待他的是進一步的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王朝的首都。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哈普斯堡的人從前門進入,自由便要離去。布魯諾又回到路上,一番長途跋涉過後,抵達那遙遠的蘇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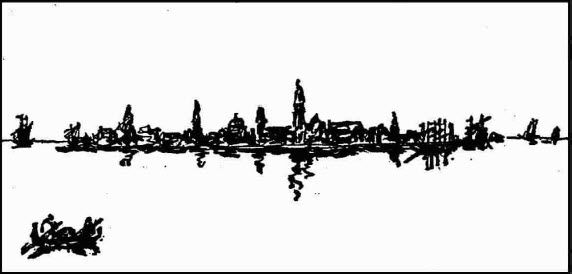
布魯諾去往威尼斯的路上
在蘇黎世,布魯諾收到一個意大利年輕人喬瓦尼·莫塞尼哥的來信,邀請他去威尼斯。我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使布魯諾接受了這個邀請。也許這個意大利農夫被一個貴族名字的光彩迷暈了,這個邀請讓他受寵若驚。
喬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輩敢於輕視蘇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卻沒有這種氣概。他是個意志薄弱的膽小鬼,當宗教法庭的官員到他的住所,要把客人帶到羅馬時,他連手指頭都沒有動一下。
通常,威尼斯政府很是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權力。布魯諾如果是個日耳曼商人或荷蘭船長,他們還會強烈抗議,如果外國軍隊敢於在他們的管轄區逮捕人,他們甚至會發起一場戰爭。可是為了一個除思想外不能給該城帶來絲毫好處的流浪漢,為什麼要去觸怒教皇呢?
的確,他稱自己為學者。共和國也備感榮幸,只是該城已經擁有不少自己的學者了。
所以,和布魯諾作別吧,願聖馬可同情他的靈魂。
布魯諾在宗教法庭的監獄裡被羈押了很多年(3)。
公元1600年2月17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燒死,骨灰隨風而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奧利(4)。懂意大利文的人可以從這個短小美妙的比喻中獲取啟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