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非洲,你瞭解得可多?恕我問你幾個小問題。
你可知道非洲的全名?
當我如此發問時,聽到的朋友先是一愣,然後漫不經心地回答——非洲不是就叫非洲嗎?難道還有其他名字?
我說,亞洲的全名叫亞細亞,歐洲的全名叫歐羅巴。南美洲叫南亞美利加洲,北美洲叫北亞美利加洲。以此類推,非洲也應該有全名的。
朋友怔了一下,緩過神後說,那不一定。凡事皆有例外。比如南極洲,肯定沒有另外的名稱。你就別賣關子了,直接說吧。
看我固執決絕的樣子,該人假裝認真思忖後說,非洲的全名,莫不是「非常之洲」?
非洲的確可以稱得上是非常之洲,但它的名字不是來自這個說法。我糾正道。
那就真是不曉得了。請告訴我吧。朋友妥協。
美國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發展項目的總監布羅蒂格姆教授,說過這樣一段不中聽的話:「根據我的觀察,在中國,關於非洲的認識極為膚淺。鮮有中國大學教授開設與非洲相關的課程,對非洲文化、歷史和政治經濟的理解也很少,因此在這個方面有著巨大的欠缺。如果你想向外走,但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又很少,這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在中國,這種文化敏感性和對投資國家的政治經濟的瞭解亟須加強。」
非洲的全名叫「阿非利加洲」。意思是:陽光灼熱的地方。我說。
關於這個名字的由來,眾說紛紜。
第一種說法:古時有位名叫阿非利加的酋長,於公元前2000年侵入北非,在那裡建立了一座城池,就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這座壯麗的城池。由於這座城市叫阿非利加,後來人們便把這座城市周圍的大片地方,也叫作了阿非利加。
第二種說法:「阿非利加」是一位女神的名字。公元前1世紀,居住在北非的柏柏爾人,在一座廟裡發現了一位身披象皮的年輕女子塑像,她名叫阿非利加。柏柏人於是拜認了這位女神做自己的守護神,然後以女神的名字「阿非利加」命名了這塊廣袤荒涼的大陸。
第三種說法:阿非利加是迦太基人常見的名字,通常認為它和腓尼基語的「塵土」相近。於是,有人認為,這片沉寂的大陸很可能是由迦太基人命名的。
第四種說法:阿非利加來源於柏柏爾人的詞彙,意為「洞穴」。原意是指在這一廣大地區,生活著穴居人。
第五種……暫且打住。關於非洲命名的由來還有許多種說法,時間有限,恕我只揀幾種常見的源頭說羅列在此。
關於名稱的起源,也許並非最重要的事情。就像人總要有個名字,不過是個符號。好在關於非洲後來的發展進程,各家的說法不再繼續紛亂——古羅馬人通過三次布匿戰爭,打敗了迦太基人,建立了阿非利加行省(這省也太大了!)。之後羅馬帝國的版圖不斷擴張,阿非利加的名字隨著羅馬人的鐵騎,瘋狂地延展並傳播。它從最初只限於特指非洲大陸的北部地區,擴大到從直布羅陀海峽至埃及的整個東北部遼闊區域。於是,人們把居住在這裡的羅馬人和本地人統統叫阿非利干,即阿非利加人。再以後,這個詞繼續野火般地蔓延不止,直到今天泛指整個非洲大陸。
讓我始終心生疑惑的是——阿非利加,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應該稱它為阿洲,不該取第二個字音命名啊。就像我們不能把亞細亞說成是細洲,不能把歐羅巴稱為羅洲。
先說說非洲的面積吧。從小學地理,講到每個省份或地區,首先就是記住面積。這很單調且需要死背,那時完全不明瞭面積的重要性,覺得就是一個枯燥的數字。隨著滄桑感的增加,才明白這個指標的重要性。找男朋友一定要問問身高,所以對於某個地域的瞭解,不知道面積,歷史就無從談起,所有的瞭解都是鏡花水月。

在地球上來來回回走了幾趟,才發現面積這個東西實在是要命的。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面積,那就是亡國。就像我們每個人揮之不去的集體無意識和祖先佔據的面積,也密切相關。泱泱大國自有妄自尊大、滿不在乎的意識沉澱在胸,彈丸小國、立錐之地的子民,多見謹小慎微、見風使舵的秉性遺傳。所以,無論你因為幼年的考試而對面積等數字多麼深惡痛絕,也請心平氣和地記住非洲的面積。
非洲大陸包括島嶼,約為3020萬平方千米,相當於三個多一點兒的中國面積。南北長約8000千米,東西長約7403千米。約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20.2%。在這塊土地上,分佈著54個國家和5個地區。
在去非洲之前,我對非洲的瞭解很有限。不瞭解並不等於沒有先入為主的印象,正是因為不瞭解,所以包括我在內的某些人的刻板成見才越發冥頑不化。
偏見這個東西的真正意思——你好奇和感興趣,但所知甚少。
早先我一想到非洲,腦海中湧出的畫面大致有這麼幾幅。
黑如漆墨的當地人、荒蕪的草原、無盡的沙漠,還有驚慌蹦跑的羚羊和懶散偉岸的雄獅……哦,說不定你也是這樣想的。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擁躉。
骨瘦如柴的百姓、鐵皮房頂的城市、艾滋病的氾濫和埃博拉的高死亡率、赤裸上身的原始部落居民和政變……哦,你是個關心世界風雲的人,每晚都會看《新聞聯播》。
如果你關注有攝影界奧斯卡之稱的「荷賽」(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簡稱「WPP」),你會記起肋骨如刀的老人、裂如龜殼的土地、倒斃的鳥禽、嘴唇上趴滿了蒼蠅的兒童……
早年間我們曾高呼過口號: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現在我們知道其中很多人過得比我們好,但也固執地相信還是有掙扎在黃連中的苦人。如果一定要你落實水深火熱的存在感,非洲大陸恐怕是當仁不讓之地。
在非洲,一位當地黑人知識分子對我說,把非洲比作一隻長長的象牙,那麼,它的兩端一點兒都不窮。南部的南非,就是一個富裕國家,它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比利時和瑞典。非洲北部的突尼斯與摩納哥,加上埃及,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真正窮苦的地方,多集中在非洲中部。
說起中非,想起1995年參加世界婦女大會時,看到非洲婦女攜帶的宣傳畫。一位老女人骷髏般地俯臥在地,衣不蔽體,週遭黃沙漫天。只有從她上翻的白眼球上,才能依稀分辨出她尚有一絲氣息游移。她瀕死的身影上,印有「埃塞俄比亞災民」字樣。
我問起埃塞俄比亞當今的狀況。非洲知識分子說那是因為當年遭了大旱,加之人禍,現在已改觀。1995年至2011年間,埃塞爾比亞的極度貧困人口減少了49%。
印象中的非洲,除了窮苦,就是酷暑難耐,幾乎不適宜人居住。追本溯源,這個看法估計來自非洲擁有撒哈拉大沙漠。它是世界上最大沙漠。不過撒哈拉大沙漠儘管很大,但並不囊括非洲的全部。就算它遮天蔽日,也只佔到非洲大陸總面積的32%。非洲其餘的面積還是適宜人居住的寶地。那些位於赤道上的國家,美若天堂。
你可能會反駁,赤道多麼炎熱啊!是的,赤道像條火繩,紅艷艷地綁在非洲腰間,但身臨其境方覺那裡並不炎熱。要知道決定自然界溫度的,除了緯度這個因素,還有個大智若愚的狠角色,那就是高度。不要忘了非洲是高原,海拔每升高1000米,氣溫就會下降6攝氏度。不可一世的緯度在溫和隆起的高度面前倒地便拜,居了下風。那些被赤道腰斬的國家,比如肯尼亞、烏干達、剛果(金)和剛果(布),還有加蓬,由於地勢較高,年平均溫度基本維持在20多攝氏度,猶如咱們雲南的昆明,四季如春。
實不相瞞,之前我還有一個詭異的想法,覺得那裡遍地行走著威風凜凜、頭插羽毛的酋長,野生動物東遊西逛、橫衝直撞……百聞不如一見,真相並非如此。即使是在非洲的國家公園和私人領地的野生動物保護區,你能不能看到種類和數量足夠多的野生動物,也完全沒有保證。一切取決於你的運氣,野生動物比想像的要稀少很多。到了非洲未曾和多種野生動物晤面,只得悻悻而返的旅人絕不在少數。只是他們大多不說,反正看見還是沒看見,只有非洲無言的天空知道。說到神秘莫測的酋長,對不起,除了在原住居民保護區看到那些身披特製服裝的表演者,真正手執權杖的土著酋長,我是一個也沒見到。很多非洲國家已漸漸跨入了現代化的門檻,少許保留下來的酋長們,無奈地隱沒在荒野深處,一般人無緣相見。印象是傳說。
最後再來說說非洲人的膚色。習慣上總是說「黑非洲」,好像非洲都是黑色人種。從南到北在非洲大陸幾萬里路(曲曲折折,把各種交通工具都算上)走下來,才發現這塊土地上更多的是混血融合的人。驚奇地發覺黑膚色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為很多層次。有黝黑發亮的炭黑、像啞光一樣能吸收所有光線的深黑、微微泛著黃色的棕黑、更為明亮的黃黑,還有稀釋如淡墨水的淺黑……無數細微的差別,讓你覺得人的皮膚原來可以如此富有層次感。常常會看見打著太陽傘出行的黑人女子。瞧著艷麗花傘下的黧黑面孔,我有時會毫無惡意地思忖——都黑成這樣子了,陽傘的用處幾近於無吧?但聽到埃塞俄比亞人非常正式地說,我們不認為自己是黑色人種,只是被曬黑的人。
非洲的人種,大而化之地說,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生活的是土生土長的非洲黑人。而在北部非洲,如阿爾及利亞、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國,是白色人種的阿拉伯人。而在馬達加斯加,則是黃種人。
在非洲度過了幾十天,實在是走馬觀花,淺嘗輒止。不過,我的若干誤解漸漸地被澄清。願把這些心得與更多的人分享。好吧,地理概況暫且說到這兒,以後我找機會再捲土重來。現在坦誠交代我為什麼要去非洲。

所有的旅行都是有前因後果的。那種所謂「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對旅行的敷衍了事和不求甚解。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旅行。越是無緣無故說走就走,原因越是隱藏很深難得破解。
2008年,我乘船環球旅行,走的是北半球航線,主打人煙稠密的亞洲、歐洲、美洲。對於非洲,只是輕輕掠過了北部,通過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本老媼決定在有生之年去一次非洲,趁眼已花耳未聾這當口兒,瞻仰這塊神秘大陸。
一個想法就像一顆橘子的種子。可惜沒有魔術師,不能讓橘子籽立刻長出綠葉,掛滿金燦燦的橘子。咱普通人對於心底的念想,能做的事兒只有積攢盤纏和等候時機。
等待這事兒,不能太著急,也不能太懈怠。太著急就容易倉皇,太懈怠了就容易碎棄。於是我開始呼風喚雨,每日興起法術——呼風就是天天早上都想想要去非洲這件事,期望吸引力法則,讓我心想事成;喚雨就是高度留心和非洲有關的一切信息,集腋成裘。
自我大興法術之後不久,收到一家旅遊雜誌的電話,說他們看到我在新浪上寫的一篇博文,內容是在加拿大尋找北極光的事。他們說很想採用這篇博文在雜誌上刊出,徵詢我的同意。此等天上掉餡餅的事兒,我自然忙不迭地表示贊同。臨放下電話的時候,對方說,畢老師可還有什麼要交代的事兒?
我很沒出息地說,除了寄樣刊,記得付稿費啊。我正在攢去非洲的盤纏呢。
對方很周到地說,稿費雖微薄,一定會速付,請放心。同期雜誌上也有關於非洲旅行的信息,您可以留意。
於是,盼著那期雜誌。不是為了自己的文章,而是為了非洲的資訊。雜誌終於到了。相關的文章是介紹一列叫作「非洲之傲」的火車,頂級奢華,終年馳騁在非洲大陸上,有多條線路可供挑選。最精彩的是它有一趟一鼓作氣穿越非洲的旅程,兩年發一趟車。我一邊看,心跳一邊加速,好像那火車噴出的白煙已經瀰漫在眼前。文章結尾處,留有一個用於聯繫「非洲之傲」中國總部的電話號碼。
我迫不及待地抓起話筒,撥通後準備一訴衷腸,不料對方是電話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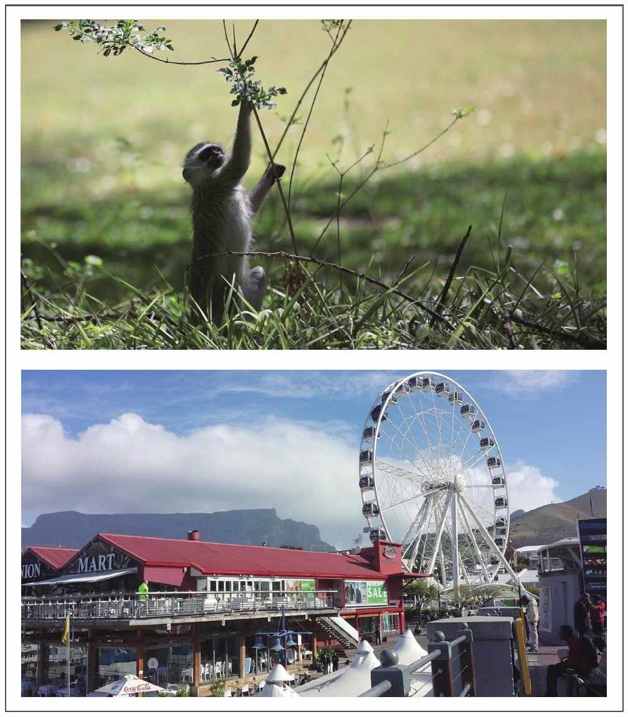
我躊躇了一下,主要是思忖好的話都是對人說的,不知道面對機器說什麼好。最後便結結巴巴地留言,說我對「非洲之傲」的旅程很有興趣,把電話號碼吐露給了那部機器。
放下電話,幾乎不抱什麼希望。一本雜誌的發行量多大啊,一定有很多人看到這則消息,一定會有很多電話打過去。這個機構肯定忙得頭昏腦漲。
晚上,我突然收到一個電話,來自新加坡。
一個很悅耳的男聲,說他是「非洲之傲」在中國的總負責人,名叫金曉旭。他聽到了我的電話留言,因為正在國外執行公務,現利用在新加坡轉機的短暫時間與我聯繫。
我一時語塞,感動得不知道說什麼好。完全沒想到這家機構的負責人會如此敬業,對一個普通的咨詢電話如此盡責。我原來準備好的一連串問題,一想到人家在國外的機場,花著高額的電話費,就問不出來了。我只是強調,我對「非洲之傲」很有興趣,很想多瞭解一點兒這個項目的情況。金先生正好要登機了,他告訴了我「非洲之傲」的網址,讓我先看看。如果有興趣,等他回京後再與我聯繫。
我放下電話,立刻打開電腦,進入了「非洲之傲」的網頁。點開首頁上的五星紅旗標誌,進入了中文界面。我一邊看,一邊屏住呼吸,生怕自己喘氣大了,吹走了好不容易得來的消息。看到每兩年一次的從南非開普敦到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的行程,原文中一句——「這是一次史詩般的旅行」,讓我頓覺喉嚨口噴湧出一股腥甜氣息。多年以來,每當我心潮澎湃之時,就會有這種心臟位置上提、動脈熱血迸射的感覺。
很久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我漸漸老邁,甚至以為自己再也不會為了什麼事情而高度激奮,沒想到這一個非洲之行的頁面就讓我血脈僨張。
我記得很清楚,就在那一瞬,我下定了非洲行的決心。無論要花費多少金錢,不管要經歷多少繁雜手續,哪怕山重水復、瘴氣橫行,我都要去非洲!
之後的準備工作,果然層出不窮非同小可。實在說,比環球旅行還複雜。環球旅行我走的是北線,主要是在第一世界發達國家轉圈,各方面的溝通和安排都比較成熟順暢。非洲則是第三世界的節奏,急不得惱不得。規則常常莫名其妙地作廢,意想不到的變故更是家常便飯。除了少安毋躁,預留出更充足的時間和將耐心打磨得更柔韌之外,別無他法。
史詩並不是那麼容易吟誦的。到非洲很遠,比到北美和歐洲都遠。萬里迢迢,就是坐北京到南非的直航,也要飛行15個小時以上。我為了節省盤纏,買的是中途轉機的票,加上在機場等候的時間,差不多要近30個小時。非洲諸項接待條件差,但旅行開銷並不便宜,幾乎和我全球游的費用旗鼓相當,要幾十萬元。再一點是非洲相對危險,除了戰亂和治安方面的問題,還有聞所未聞的傳染病。我有一個朋友的弟弟到非洲執行公務,在當地得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腦炎,人事不省地運回國,雖經大力救治,還是在昏迷了一年之後與世長辭。
非常感謝金曉旭先生,他淵博的知識和勤勉的工作態度,給予了我巨大的幫助。如果沒有他,我的這趟「史詩般的旅行」,剛起筆第一行就得夭折。特別是當我疲於奔命實在應對不了規劃旅途的無數煩瑣細節,準備放棄某些重要項目的時候,他的苦口婆心和諄諄告誡,類乎指路明燈。他溫暖的提點,讓我重新燃起希望。他周密的安排,讓我對這趟未知的旅程增強了信心。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金曉旭先生,就沒有我的非洲之行,也不會有這本書的問世。對此,我深深感謝並銘記心間。
終於,一切準備停當。我注射了預防黃熱病的疫苗,口服了預防霍亂的丸劑,懷揣著治療惡性瘧疾的青蒿素,帶著各種驅蚊劑和藥品,加上簡單的幾件行裝,一咬牙一跺腳,出發啦。目的地——阿非利加洲!
